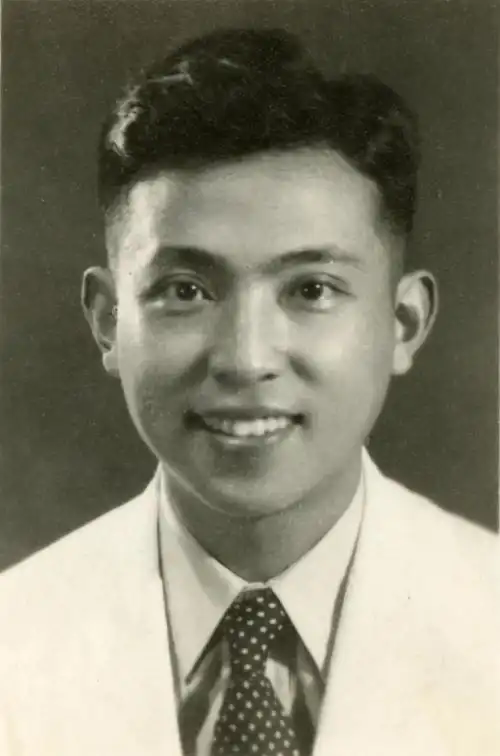
1949年8月,穆旦离开泰国曼谷,去了美国,开始了他的美国留学。这个时间正是国共内战几近见出分晓,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很容易让人将这与穆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联系,进而产生一些联想,而且还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此前穆旦会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选择离开?”(易彬:《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292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有人联系到穆旦曾经与国民党之间说不清的关系,觉得这是穆旦明智的选择。不过,这一说法很快就被穆旦在四年后的回国之举所否定。其实,关于穆旦的出走与归来,是很复杂的,既有他对政治的某些复杂的认识,又有他的学业和生活上的某些细微的原因,还可能存在某些外在因素对他的影响。因此,梳理并讨论穆旦的出走与归来的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
易彬将穆旦的出走念头追溯到穆旦于1947年10月所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标题就是“我想要走”,而且易彬在他的《穆旦评传》中全文引了这首诗,让我们可以了解出走前的将近两年的时间里穆旦的心理状态。读了穆旦这首诗,不难看出他对现实的极度厌恶和对环境的严重不满,内心感到十分绝望,于是产生了逃离的急切欲望。然而,离开并非易事,否则他就不会再经受将近两年的煎熬了。一个人要想离开生活已久的环境,首先需要找到适合去的地方,也就是说到哪里去才能令自己的身心感到舒畅。其次是怎样才能到达。再次是是否具备到达的条件。成人与儿童不同,考虑的现实问题比较多。中年人与青年人不一样,不会不顾一切地追求某个事物,相对来说理性更强一些。生于1918年的穆旦,到他写下《我想要走》时已经是将近30岁的年龄了,虽然不能完全说是中年人,却也是由青年向中年过渡了。他想走,就不能不考虑上面这些问题,他先得研究时局,尽量搞清楚历史未来的发展走向。当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将来谁胜谁负,还难以看清,尤其是胜利的一方究竟将国家带向何处,都令人难以捉摸。同时,他的从军经历和诗歌翻译与写作将来对他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影响,也令他感到困惑和迷茫。如果是国民党在内战中获胜,这些事或许不会对他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如果是共产党在内战中成为胜利的一方,他的那些经历说不定就会成为历史的包袱。与此同时,穆旦还想到中国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之根在中国,离开了中国就等于断了自己的根,他虽然是现代知识分子,还具有报效祖国的热血。还有赡养父母以及与未婚妻的协调等事务也一直令他难以拿定主意。经过二十几个月的观察和思索,穆旦最终还是下了决心去美国留学。
穆旦去了美国,而且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议论。有人可能认为他是出去“政治避难”,有人觉得他这是逃亡行为,还有人将其视为正常的出国,不必过度解读。据我看来,“政治避难”说固然不能完全否定,却也不必夸大。穆旦不仅参加了国民党的远征军,而且还与不少国民党人士有过交往,更重要的是他所接受的是欧美式的教育,思想意识偏向于西方,与共产党的政治理念有些相左,而他后来归国后的遭遇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不过,穆旦在出国前虽然生活上遇到不小的困难,心情也不好,但是毕竟还没有遭受政治迫害,因而说他要出去“政治避难”根本就讲不通。如果说他对共产党怀有恐惧,他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可以跟随国民党到台湾去;二是可以到香港谋生;三是可以到东南亚的某个国家进入大学任教;四是还可以去欧洲搞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况且,穆旦根本就没有向任何机构申请过“政治避难”。至于“逃亡”更是谈不上,因为穆旦没有遭到追捕,他到美国去是为了读书留学,虽然含有逃避的意义,但总的来说还是自主选择。如果说穆旦去了美国是正常出国,却也不完全如此,毕竟是在政权更替之际。所以,易彬称穆旦去美国为“出走”(第270页)是很恰当的。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穆旦在美国过了几年,居然回国了,也就是易彬所说的“归来”(第270页)。新中国成立之初,确实有许多留学或者工作于欧美的知识分子回国,他们的具体回国情形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受到祖国新的气象所感召,在热爱祖国强烈的情感推动下,慷慨激昂地投入祖国的建设之中。然而,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头脑比较清醒,对于政治的判断比较准确,一直待在国外,直到数十年后才荣耀地回国探亲访问。就穆旦的情况来说,他不像老舍那样妻儿与情人都在国内,赵清阁用一封信就将老舍召了回国;他也不同于钱学森,由于政治因素的缠绕而不得已回国,他是自己出走几年后所作出的又一次选择,而且他的这一选择并非一时冲动所致,而是作了长时间的充分准备。据穆旦妻子周与良说,他选择回国的主要原因是,留学生的生活非常艰苦,“当时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必须半工半读,每个中国留学生都要做临时工。良铮(即穆旦——引者注)为了少费时间多挣钱,不愿在大学里干活。”(第279页)穆旦在他后来的回忆性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其实,经济困难只是穆旦回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当时留学生既然生活都很清苦,那么为什么没有全部回国呢?更何况留学时间不会太长,很快就会过去,毕业后找到工作,经济状况很快就会得到很大改善。值得注意的是,穆旦在留学第二年就选修俄文和俄国文学。此时,穆旦已经获得了美国国务院中国留学生救济金。本来,学生选修什么课应该来自兴趣,但是在穆旦这里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说俄罗斯文学还出现了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等世界级的大师,那么苏联时期的文学就很难说了,高度极权之下的苏联文学除了政治正确之外,究竟能有什么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呢!关键是苏联与中共之间超亲密的关系,而且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新政权,而且还推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所谓“一边倒”,就是要倒进苏联“老大哥”的怀抱。所以,穆旦选修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并且还悄悄地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同时,穆旦还写了《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这样批判美国社会的诗作,显然是在为回国做准备,他要通过这些方式拉近与中共的关系,或者说将来可以更好地适应回国的工作与生活。穆旦的想法确实有些幼稚,他将纷繁复杂的政治看得太简单了。不过,他也只能这样做了。他要想回到中国大陆,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既然已经到了美国学习,穆旦为什么一定要回国呢?他如果下定决心留在美国,或者到欧洲乃至香港,不回中国大陆,完全可能,也就没有必要通过选修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来与中国新政权套近乎。对于这个原因,易彬是作了一番探讨的。他借用张新颖教授提供的材料,进而推断出穆旦留美时的学习成绩不够理想。张新颖的材料显示,穆旦在芝加哥大学毕业选择的不是做论文,而是通过考试。然而,他“考了两次方才通过”(第285页),而且考试成绩“B居多,美国文学史居然是C”(第285页)。这似乎与鲁迅在仙台读书的情形比较相似,学习成绩都不那么理想,一个“弃医从文”,一个选择回国。这个道理似乎成立,但是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显得穆旦回国有些被动,因而只能算是穆旦回国的原因之一,而不是根本原因。易彬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也不得不表示:“穆旦内心更为隐秘的想法却还无从窥见。”(第290页)还有一种说法,穆旦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诗人,他的创作虽然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但是他的创作文化之根在祖国,他的读者也在祖国,他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似乎有断了根的感觉。他从自己的创作需要出发,以诗人的天真想象着将来的创作可以大显身手,于是想到了回国。这个原因很符合诗人的特性,而且结合前面所讲的他的行为,其情感逻辑也还是说得通的,可惜的是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

另外,还有一点也应该值得注意,穆旦虽然在西南联大读了大学,而且还参加了远征军,征战缅北野人山,与不少国民党人士有所交往,但是他基本处于社会底层,生活常常处于困难境地,到了美国留学,虽然毕业后经济状况可能得到极大的改善,然而在读书时经济常常让他感到窘迫。而贫困中的人很容易对现实不满,思想也就极易向“左”转。当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之后,穆旦的潜意识中可能以为新政权可以改变自己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他可以在诗歌创作上大显身手,另一方面他的社会地位可能有所提高并且得到巩固。因而,在回国之前,他就和他的好朋友巫宁坤一样,“渴望出现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第290页),“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迟早要回国,用我的专长为一个新中国服务”(第290页),于是将自己曾经的历史淡忘了,以为不会有什么事,于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共出版的《群众与主流》杂志,在书店里到处搜罗‘进步’书刊”(第291页)……巫宁坤所叙述的是自己的经历,却也符合当年穆旦的实际情况,那时的穆旦虽然不会与巫宁坤的阅读完全相同,但是他们一对好朋友相互影响与趋同还是没有问题的。
1953年初,穆旦终于回国了,据说“冲破重重阻力”(第292页),可见,他回国的决心之大。但是,他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厄运。他以诗人的浪漫想象着回国后的种种情景并没有出现,特别是他想象到的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现代国家的建设原来不过是假象,而在这假象的背后却是对他们这些“海龟”们的不信任。于是,他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被审查回国的动机与目的。其实,穆旦虽然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与苏俄文学,阅读了一些革命理论著作,但是根本就不了解共产党,对于他所投入的社会主义体制,对于新政权本质的了解和认识十分肤浅。就这一点而言,穆旦不如他的另一位好朋友李政道。尽管李政道比穆旦年轻一些(穆旦出生于1918年,李政道出生于1926年),但是他的目光更敏锐,他看清楚了祖国大陆的现实,留在了美国,在那个“南渡北归”的年代作出了明智的选择。穆旦虽然得到了李政道的劝告,还是决定回国。
穆旦刚刚回国,就收到组织上发给他的一份表格《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被要求填写。这份表格看名称具有某种麻痹作用,看上去似乎是为分配工作提供方便的,实际上却是利用他们对组织上的信任对他们这些留学欧美归来人员展开调查,要他们必须认真填写“在国内外参加过何种社会活动”(第300页)、“回国经历情形”(第300页)、“在国外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回国动机”(第300页)、“你在回国后有何感想”(第300页)等等。让穆旦他们填写这样的表格,就是要摸他们的底,为后面展开对他们的控制等一系列工作做准备。当时,穆旦还处于回国的兴奋之中,根本没有想到表格背后可能隐藏的东西,所以将表格中的各项都认认真真地填了。
穆旦回国之初的意愿就是搞俄语文学翻译,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介绍给读者,他既不想在机关工作,也不想到大学教书。他还没有意识到在新中国,个人是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的,不仅不能选择工作的内容,而且不能选择工作的地点和单位,更没有给他“单干”的自由。他不知道,新政权就是要将每个人都纳入到体制中来,必须接受体制的规训和管制。穆旦见无法自己“单干”,就想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搞点写作和研究,但是“未获成功”(第301页),最终只能到南开大学任教。穆旦这是回到了母校,从情感上说也不错,尽管此时的南开与当年的南开并非一回事,况且天津还是他的出生地。这让穆旦似乎得到了补偿。
穆旦进入南开之后,在工作之余以极大的热情翻译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及其理论。不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翻译与介绍同现实需要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从现实需要出发,穆旦应该以翻译介绍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为主,因为苏联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文学作品与理论在意识形态上与现实完全一致,或者说正符合当局教育与宣传的需要。然而。穆旦翻译的却是以普希金的作品为主,当然,普希金的作品很受读者的欢迎,但是未必符合当局的胃口,也就是说和当局的需要存在一定的距离。
既然不完全符合当局的需要,那么穆旦这些“海龟”们就得同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一道接受思想改造,就得安排他们参加“政治学习”。所谓的政治学习,就是将这些知识分子(无论是“海龟”,还是旧知识分子)集中起来听报告,听读文件和报纸上的文章,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他们进行政治洗脑。而且,参加这样的政治学习是“硬性规定”(第306页),不得请假。据穆旦的好朋友巫宁坤回忆:通过学习,他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第306页)。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表现出十分认真的态度,既要做出全神贯注听讲的样子,又要细致地做笔记,准备所谓的考试。通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都很真挚。”(第305页)巫宁坤是留美回来的学生,而且还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所以无论是在民国,还是在美国,都生活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中,而这时却失去了言论自由,让人很难适应,因而他“越来越公开地对缺少言论自由表示不满”(第306页)。巫宁坤说的是自己的感受,同时他也认为穆旦与他“有同感”(第306-307页)。
当时的穆旦虽然与巫宁坤对于现实“有同感”,但是能否像巫宁坤一样敢于公开表示不满,就很难说了。不过,他肯定不会被当局认作自己人,当然也就不会得到信任和重用。而那些领导们从身份上说可能也是知识分子,但都已被政治化了,基本上都是城府极深的,而且善于等待和捕捉时机。所以,穆旦在进入南开之后的最初一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过着“看似平静的生活”(第314页)。
终于在1954年,穆旦的“看似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这一年初冬,南开大学发生了“外文系事件”(第320页)。这件事情实际上只是复杂的人际关系所引起的冲突。像这样的事件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外国,都可能发生,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和调解,总不会闹到政治上去。就是在民国时期发生过驱逐闻一多等人的学潮,至多让被驱逐者走人而已,而被驱逐者换个地方照样教书,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受政治利用的学潮驱逐校长们则另当别论。然而,在1950年代的大学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让知识分子自己解决,而且还将其政治化,从而成为当局将政治大棒挥向需要整肃对象的一个契机。于是,所谓的“外文系事件”到了领导这里竟演变成一场不大不小的整人运动。穆旦等人也就被指责为小团伙,“挑衅群众与领导的关系”(“挑衅”应为“挑拨”——引者,第327页),成为“反对系的领导”(第327页)的坏人。既然如此,具有专业斗争才干的领导们建立起“‘进步人士’的组织”(第329页),让已被收复的知识分子卧底,让这些卧底分子密切接触穆旦等人,并“及时汇报和建议”(第329页),广泛搜集材料,以便将来算账。于是,周基堃主地请缨,再三要求“向‘党总支同志’作《报告和请示》”(第329页),并且“保证细心体会党的政策坚决投入我自认为是党和人民利益的当前战斗”(第329页)。经过一番充分地搜集整理材料,校方终于整理出了一个反对领导的小集团来。穆旦虽然没有被列为小集团的头目,却也是逃不脱的一员。到了这个时候,一所在全国影响巨大的大学不以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为己任,却专事于整人搞运动,堕落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绞肉机。根据学生所提的意见,穆旦所涉及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但在领导们这里却成为整人的宝贝。于是他们频繁地召开了所谓的“谈心会”和“座谈会”,看似十分亲切和温和,却暗藏杀机,就是通过一副和善的面孔将人们内心深处的东西给“钓”出来,挖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学校方面形成了处理意见,对于穆旦来说,这个意见还是比较轻的,大概是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还没有到来的缘故吧,领导只是批评他“表现是粗暴的,受人怂恿的”(第336页),并且要求他“从这次事件吸取教训,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并应与一切‘影响工作,破坏团结’的行为断绝关系”(第336页),暂时放他一马,没有给他扣上大帽子。
虽说暂时放了穆旦一马,并不等于他就完全没事。穆旦在“外文系事件”上刚被放过,他的所谓“私人翻译”却又被人提了出来。本来,翻译是穆旦的工作之外的事情,即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只要翻译对象不是“反动派”,内容不“反动”,只要不影响教学工作,那就是个人的权利。但是,偏偏有人受到政治环境的诱惑与怂恿,向有关机关递送了书面材料,“检举了穆旦所谈到的他今后的职业问题,其中谈到朋友们都反对他搞‘个人’翻译。”(第344页)。有人告密,就有人调查。易彬的传记虽然没有记述调查的结果,但是已经对传主的心理和翻译行为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就是说,不仅个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而且令穆旦长期生活在阴影之中,时时刻刻心怀恐惧。
心理恐惧不仅仅是因个人翻译受到了调查。更在于大张旗鼓地“肃反运动”与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风运动。穆旦由于参加了远征军,虽然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新政权之下居然成为罪过,理由是远征军属于国民党的军队,于是,穆旦便成为了肃反对象。此时,穆旦虽然没有被抓起来坐牢,然而内心的恐惧是可以想象的。这个时候,他很可能想到那些仍然待在国外的同学与朋友根本不会遭遇到这些烦恼,如果想到这些,他会不会为回国之举而后悔呢?
1957年春天,穆旦的心情舒展了一段时间,那是因为最高领导推动了“双百”方针,营造出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穆旦此时虽然年近四十,但是对于现实的认识仍然十分单纯,不要说他,就是许多人生经历都很丰富的人都未能看出其背后的“阳谋”,所以信以为真,以为以后的政治越来越开明,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社会现实越来越文明,国家越来越现代化。可是,仅仅过了几个月,政治便急转直下,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穆旦在以为开明的时期发表的《九十九家争鸣记》等诗歌无疑给人家留下了把柄,成为人家斗争和整治他的靶子,他那些不合时宜的诗歌居然能够发表,却没有想到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他在随即爆发的运动中被持续批判了“一年多”(第373页)。曾经发表穆旦诗作的《诗刊》此时出版了“反右派斗争专辑”(第373页)。这个专辑虽然不是以穆旦为主要批判对象,但是已有人批判他的诗歌“流露了比较严重的灰暗情绪”(第374页),“几乎是一个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诬蔑”(第374页),并且警告他“从这种阴暗的情绪出发,他的诗必然会歪曲甚至会诬蔑现实生活攻击新的社会”(第374页)。紧随其后的《人民文学》在10月号上以“自我清算”的方式为发表穆旦那些“令人不知所云”(第374页)的诗作而检讨。《人民文学》虽然没有直接批判,但是对穆旦的创作显然也给予了贬损。到了年底,《诗刊》发表了安旗的批判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安旗以穆旦的诗歌为例,将“‘晦涩’与‘现代主义’画上等号”(第375页),指责穆旦“成为脱离‘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没有‘真正的思想内容’的、‘资产阶级’的‘莠草’”(第375页),从此开始给穆旦诗歌创作扣上政治性的大帽子。到了这个时候,最高报纸《人民日报》登场了,发表戴伯健的文章,专门对穆旦诗歌展开批判,文章以“反诘句式”严厉责问,进而暗示穆旦的创作动机存在严重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批判,穆旦似乎就成了“反党分子”,到了1958年年底,穆旦居然被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决为“大肆向党进攻,在人民日报发表《九九家争鸣记》反动文章”(第377页)。
穆旦受到了批判,没有作出申辩,于是做起了检讨。这在当时,做检讨是知识分子的常态,至于是否真正认为自己错了,该受惩罚,各人情况不同,内心想法肯定也不一样。不过,既然是做检讨,特别是迫不得已的,那就放弃自己的信念和人格尊严,承认自己的所谓“罪错”,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痛改前非。也有人以检讨的方式为自己辩解,当然,这需要艺术。穆旦做检讨显然为形势所逼,他承认自己有错,不过只是“局部性地承认错误”(第378页),还为自己的创作作了辩护。其实,事实就是如此,穆旦说的也是实话——如果不是中共中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也不会写那些诗歌,更不会拿出去发表。穆旦的这种态度当然不会让领导们满意,他们必须要令穆旦臣服。于是加紧对他的精神围剿。参与围剿的不仅有邵荃麟、徐迟等文坛诗坛大腕,而且还有所谓的工人与战士这些诗歌“门外之人”(第380页)。虽说邵荃麟与徐迟的批判多少有些保留,而且还包含应景的成分,但是毕竟对穆旦的精神形成了威慑,穆旦也因此沦落为罪人。于是,他被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三年”(第309页),给他定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第309页)。不过,南开对于穆旦还是比较照顾的,既没有将他下放到什么农场或工场去劳动改造,也没有罚他去清扫街道或者打扫厕所,而是安排他到图书馆做英文编目,虽然不能教书或者搞翻译与创作,但是毕竟没有离开图书。即使如此,穆旦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扭曲。他在1959年9月底的日记中做了比较详细的思想总结,尤其突出的是就“如何作党的‘驯服工具’”(第409页)谈了具体的三点认识。本来,日记是私人空间,是其主人的内心独语并记述其日常感受,具有很强的私密性,但是穆旦的日记却变成了向组织上交心的载体。其中尤其令人震惊的是,穆旦对于自由的理解和认识:“自由有两种:为所欲为、损人利己的自由,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的,但却有合理发展个性的自由。你只要以党的方向为自己的方向,即感到自由。”(第409页)穆旦的这两条自由,前一条是对自由内涵的严重曲解,后一条虽然提到了“合理发展个性”的问题,但只是一闪而过,随即转到了“党的方向”来,实际上是对党的归顺和服从,是向权力的屈服。其实,真正的自由,必须以独立为基础,仰仗于他人,顺从于权威,屈服于权力,根本谈不上自由。穆旦对自由的认识完全陷入了误区,与他的人生经历及其学历实在配不上。
不过,我在读到这样的日记时还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希望他只是借日记的形式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来保护自己,他心里明白,当时记下文字的东西很容易被人偷窥或者查抄,这样,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辩解了。但是组织上没有轻易放过他,要求他“交代、交代、再交代……”(第413页)。这种“看起来却是无止境的”(第413页)“交代”毫无疑问就是对他的精神折磨,就像是著名女作家杨绛小说中所描绘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洗澡”那样,无论是“大盆”还是“小盆”,都必须过了所谓的群众这一关,否则就要没完没了地无休止地一直洗下去。经过这样的折磨,知识分子的不仅失去了人格尊严,听任权力的任意摆布,而且丧失了思想信念,变成一个时代的“死魂灵”。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作为“历史反革命”的穆旦自然无法逃脱,等待他的是“更大的梦魇”(第420页)。他“被集中劳改,被批斗,家庭受到很大的冲击”(第420页)。最令他痛心的是,凝聚着他心血的图书和文稿在这场浩劫中被抢、被扔与被毁。几经折腾,年仅52岁的他“看起来‘已经是个老人了’”(第428页)。如果这只是形貌上与肉体上的衰老,那么他的精神与灵魂更加衰老,他自己在1968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认罪必须扎根在思想上,这是根本的。”(第425页)穆旦自己居然要“认罪”了,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呢?是参加抗日远征军吗?是翻译普希金等人的诗歌吗?是创作诗歌吗?是在南开教书吗?……说来说去,穆旦根本就没有犯下任何罪,可是他为环境所逼要承认“犯罪”。
1977年年初,穆旦不幸病逝,其时他才59周岁,这在20世纪的现代社会里不算高寿,对于许多人来说,晚年才刚刚开始,但是他离开了人世。试想,如果不是受到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他可能活得更长久一些;如果他一直生活在海外,成为更杰出的诗人或者学者,或许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甚至百岁,可是他因回国归来却在60岁不到的年龄就去世了,回顾他这短暂的一生,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他为五十年代的回国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2023年9月5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
名人透视070:因苦难而升华的莫言
名人透视069:民国教父宋耀如
名人透视068:“马列主义老太太”杨沫
名人透视067:螺丝钉阳翰笙
名人透视066:乱世才女苏青
名人透视065:鲁迅是谁?
名人透视064:流浪者三毛
名人透视063:“两面人”老舍
名人透视062:两个柳青
名人透视061:“力争跟上时代”的俞平伯
名人透视060:李广田的“遗恨”
名人透视059:“老运动员”公木
名人透视058:浪漫多情郁达夫
名人透视057:快乐王蒙
名人透视056:可敬可鄙的周扬
名人透视055:看啊,天边那片云
名人透视054:拒赴延安的艾芜
名人透视053:荆棘中的独立
名人透视052:交出自由的陈白尘
名人透视051:灰娃的天问
名人透视050:滑入炼狱的乔典运
名人透视049:花瓶冰心
名人透视048:糊涂周作人
名人透视047:好人茅盾
名人透视046:“乖僻”残雪
名人透视045:孤魂萧红
名人透视045:李健吾:书生的政治情结
名人透视044:尴尬沙汀
名人透视043:冯雪峰:浪漫纯真与命运悲剧
名人透视042:废了文功的沈从文
名人透视041:非主流的张恨水
名人透视040:翻越人生大山的路遥
名人透视039:多维贾平凹
名人透视038:多变章太炎
名人透视037:断绝友情的萧乾
名人透视036:第二种忠诚
名人透视036:邓拓:从宣传家到作家
名人透视035:“刀尖上跳舞”的程树榛
名人透视034:大彻大悟的牛汉
名人透视033: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丁玲
名人透视032:从“弃儿”到香饽饽的王学忠
名人透视031:从怀疑出发的林昭
名人透视030:从“农民诗人”到“向阳”诗人的臧克家
名人透视029:纯真顾城
名人透视028:“纯文学”才女林海音
名人透视027:纯粹文人邵洵美
名人透视026:传统文人柳亚子
名人透视025:冲破规训的顾准
名人透视024:超越意识形态的爱国者
名人透视023:“超现实主义”的艾青
名人透视022:曹禺的自我否定
名人透视021:步入深渊的徐铸成
名人透视020:被压抑的欢呼
名人透视019:被汉奸的刘鹗
名人透视018:不愿忏悔的夏衍
名人透视017:不合时宜的独立自尊
名人透视016:被撕裂的何其芳
名人透视015:美丽的噩梦
名人透视014:不对称的爱情与婚姻
名人透视013:并非浪漫的郭沫若
名人透视012:辫子辜鸿铭
名人透视011:被灼伤的爱情
名人透视010:被“战犯”的胡适
名人透视009:被规训了的浩然
名人透视008:被亲情绑架的朱东润
名人透视007:徐志摩与陆小曼
名人透视006:悲哀余秋雨
名人透视005:挨骂的郑振铎
名人透视004:“历史的误会”的瞿秋白
名人透视003:“宪政迷”梁启超
名人透视002:饱受委屈的端木蕻良
名人透视001:爱情教母琼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