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稚写作
“五七干校气象新,/“三同”“四好”意义深。/反帝防修千年计,/加强牢固在基层。/养猪种菜英雄业,/园地猪圈一战场。/深明动植辨证理,/胜利才能有保障。/夏麦明黄豆苗青,/田里农活不暂停,/采桑种棉赶时令,/愧杀穿衣吃饭人。”(李扬《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99页。)
读了上面所录的这首诗,我们很难将它与文学大师沈从文联系起来,怎么也想不到是沈从文的大作。然而这恰恰是70年代初他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所作的《新认识》。坦率地讲,这首《新认识》不仅表现了作者在意识形态上与官方保持高度一致,而且缺乏诗的意境和味道,就和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所写的应时应景诗差不多。读到这样作品,我们不禁要问,当年被鲁迅称为“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17页。)的沈从文怎么会写出这样的烂诗?由此,人们可能会联想到郭沫若。五四时期令许多青年十分崇拜的郭沫若创作出《凤凰涅槃》、《天狗》等辉煌的传世之作,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只能写出令人作呕的《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之类的阿谀奉承之作,于是对郭沫若的人格提出了质疑。然而,沈从文不同于郭沫若,他写《新认识》和《好八连》这些诗歌的时候,与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忆向阳》中的那些诗作一样,都是真实情感的抒发。问题是沈从文的这些作品根本不能与臧克家“向阳”诗作相比,这让人看到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他的文学功夫已经被废了。
一个武术家最悲哀的事莫过于他的武功被彻底地废掉,这意味着他在武林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对于作家来说,最悲哀的事情不是被捕入狱,不是遭受批判和围剿,而是文功遭废。一个作家一旦失去了写作能力,那就意味着他文学生命的终结,意味着作家的称号已经属于过去。对于沈从文来说,他的作家身份到了1949年就被中断了,后来他虽然很想通过努力再创辉煌,无奈力不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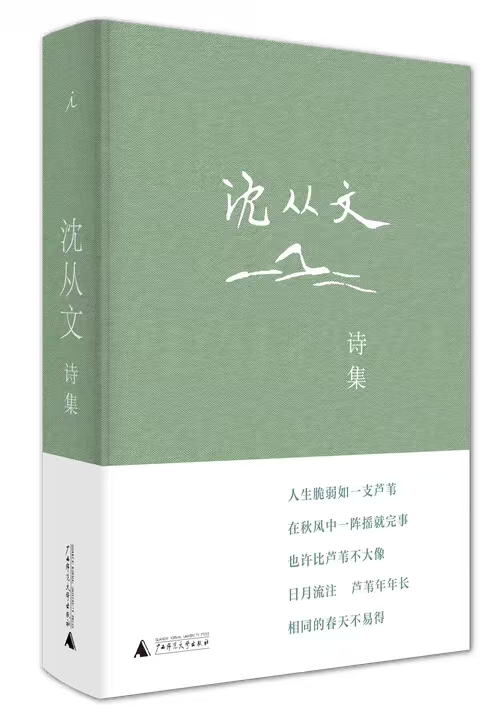
遭受厄运
1948年3月,郭沫若在《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发表了《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列为批判对象,该刊同期还刊发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与邵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同样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沈从文。这些批判文章虽然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但是却代表着左翼革命阵营对沈从文的政治宣判。特别是郭沫若在左翼革命阵营中已经被树为继鲁迅之后的文化旗手,他的文章更是代表即将建立新政权的中共的态度。于是,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根本没有沈从文的位置。与此同时,他还遭受解放区报刊的严厉批判。所以,当新中国成立之际,沈从文陷入了极度不安和疑惧乃至精神恍惚之中。本来,就在国民党撤退大陆前夕,沈从文已经被列进了“抢救”北方学人的名单之中,国民党当局给他提供了南下的飞机票,但是沈从文没有随国民党南下,而是留了下来。他尽管对未来的新政权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他对国民党印象并不怎么好,非常厌倦国民党的统治,而且曾经得罪过国民党,同时他还有过十分幼稚的想法,根据多年来的人生经验他认为:“尽管自己对政府颇有微词,但最坏的结果也只不过是书籍被禁毁,怎么着也不会影响到生计问题。我写我的,你禁你的就是了,总不能把我的作品全都禁了吧?”(李扬:《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第40页。)显然,沈从文这是以过去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经验想象着新社会自己的未来,根本没有想到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别,更没想到中共对待不喜欢的作家作品所采取的措施与国民党的方式截然不同。此外,沈从文在共产党内还有丁玲、吴晗、何其芳、乐黛云等一批朋友。殊不知,他的这种人生选择却将他推上了文功遭到废弃的路途,这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尽管他内心感到迷茫和苦闷,“预感到自己的写作方式与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格格不入,最终的结局恐怕是‘被迫搁笔’”(李扬:《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第39页。),但是他还是从国家与民族利益出发来应对眼前的历史剧变。
然而,历史并没有因为他胸怀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对他有所宽容,反而越来越对他形成逼迫。当然,中共并不像国民党那样愚蠢地查禁和审查,而是以非常高明的方式逐步废弃他的文功。首先,在新政权成立之前,沈从文的作品就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宣判了死刑”。(李扬:《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第44页。)这样的死刑宣判由于来自青年学生,令沈从文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虽然可能意识到这些青年学生的态度来自一股政治势力,然而其行为十分巧妙而让他无可奈何,令他紧张和不安,内心感到强大的压力。面对着这种无形的压力,他找不到抗争的对象,就像鲁迅所说的陷入了“无物之阵”。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并不因此而罢休,他们还贴出大幅标语,将他视为第三条路线的代表要予以打倒。革命势力高明就高明在不以行政的方式处理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而是通过青年学生发动斗争,进而对他发出严厉的警告:不要再以原来的方式进行创作!赶紧转向革命的一边搞创作!否则就是反动作家,就要遭到更严厉的斗争。对于身处这样的尴尬境地,沈从文进行了反思,“他想从自己的作品中为郭沫若寻找自己反动的证据,但越看越糊涂,越看越难受。”(李扬:《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第47页。)于是,沈从文在极度的恐慌和困惑中,感到一张无形的巨网正向他扑来,并且慢慢收紧。沈从文的这种恐慌和惧怕心理或许正是有关方面所需要的。一个作家在愤怒、悲痛、苦闷、挹郁、忧愁的心境中都可以进行创作,并且可以创作出杰出的作品,惟独在恐慌和惧怕精神状态下怎么也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恐慌和惧怕中的沈从文尽管经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没有对新政权采取对抗的态度,而是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想,竭尽全力试图融入新社会,与新政权建立友善的关系。与此同时,新政权也没有将沈从文排到敌人的行列,先前让青年学生批判他,只是给他一个严重的警告,希望他不要滑到敌人的那边。既然沈从文在文学界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如果将他改造过来,为自己所用,倒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于是,革命阵营就在北平解放之际,马上有人来做沈从文的思想工作。1949年2月上旬,北平刚刚宣告和平解放,张以瑛就从天津赶来看望沈从文。这个张以瑛一方面是夫人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的女儿,另一方面又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她来看望沈从文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探亲,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沈从文努力适应新的社会。后来,东北野战军后勤政委、党委书记陈沂得知沈从文的精神状态后,一方面马上给沈从文寄来了“进步”书刊,一方面到沈从文家来与他进行深入的交谈,“让他相信党,不要总是疑神疑鬼。”(李扬:《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第63页。)随后,陈沂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建议继续帮助沈从文实现思想与创作的转变。但是,沈从文一时转不过思想的弯子,内心的阴霾仍然没有驱散,他深切地感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他还无法融进新的社会,他不知道以后到底该怎么办,于是他绝望了,绝望中他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血管,又喝了些煤油……由于被发现及时,得到及时抢救,沈从文才被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然而他的内心却仍然没有摆脱严重的危机。
当时,像沈从文这样陷入精神危机和创作困境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为了“帮助”他们融入新社会,有关方面将他们安排到中央革命大学培训学习,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教育“帮助”他们转过思想的弯子,进而对新政权产生认同感。于是在10个月的学习期间中,“听政治报告,学习各种政治文件,讨论,座谈,对照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检查、反省、再认识,是学员们每天的课目。”(凌宇:《沈从文传》,第426页。)渐渐地,沈从文的思想意识产生变化,开始认同当局的意识形态,并且以其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与此同时,开始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反复审视自己走过来的人生道路和过去的作品,进而否定自己过去的创作,他的那些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在一个动的社会中,历史伟大的变革过程中,人民革命向前发展中,可以说毫无意义可言,是应当随同旧社会一齐埋葬,才不至于还有不健全影响的。”(沈从文:《总结·思想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121页。)就在这段学习期间,在这思想扭转的过程中,大多数学员为自己的思想转变而欣喜,以跳舞的方式放松自己庆祝新生。沈从文没有加入到跳舞的行列中来,他却跑到厨房做起了帮橱工作。在帮橱中,沈从文结识了一位炊事员,他与沈从文一样都有过行伍的人生经历。这使他们十分亲近,于是两人常常在聊天交谈。炊事员向沈从文叙述了自己的人生,进而激起了沈从文的创作欲望,不久,他写成了小说《老同志》。小说写成后,沈从文再看这篇作品,感到非常不满意。一方面,他从官方的意识形态来审视这部小说,觉得现在的创作“只醉心于与这个伟大时代不相称的人生琐屑”。(凌宇:《沈从文传》,第428页。)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此时所写的东西“已经很难见到他往日小说的神韵了。”(李扬《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第89页。)一段时间以来,他对小说作了反复修改,并且不断地往外投稿,然而屡遭退回。1952年,他将稿子寄给老朋友丁玲,恳求她“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的名字也好。”(1952年8月8日致丁玲,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295页)为了发表作品,沈从文几近哀求了。这种有伤尊严的乞求反映了沈从文内心的严重焦虑,他是多么想重返文坛,回到作家的行列中来啊。然而这部作品很可能由于不合时宜也有可能没有达到发表水平而最终未能与读者见面。这样,作为作家的他开始从文坛上消失,而他本人经过3年的犹豫、彷徨和挣扎之后逐渐找到了新社会生存的通行证,也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岗位——和文物打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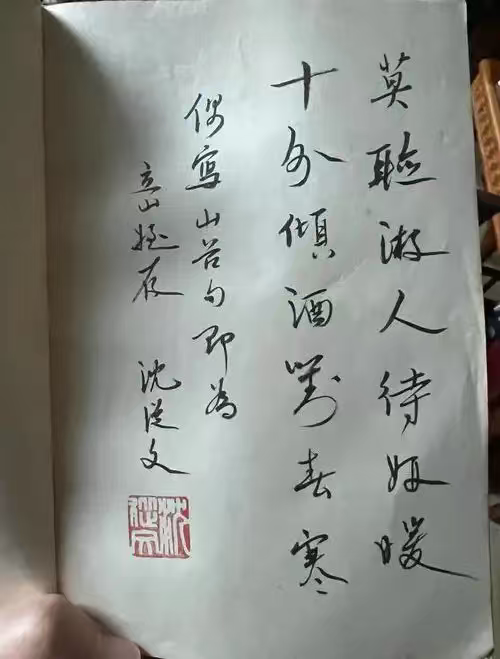
边缘人生
与文物打交道,可以说是沈从文最明智的人生选择。且不说他早年行伍时就与文物打过交道,拥有比较丰富的文物知识,最关键的是与文学相比,搞文物鉴赏和研究更远离政治风暴,然而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过,按照沈从文当时的认识,就是能够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看看他过去的那些作家朋友,后来在反右与“文革”当中轻的遭到批斗、流放,重的被凌辱和殴打,甚至被迫害致死。丁玲在反右运动中被揪出来“再批判”,后来流放到环境十分恶劣的北大荒,又惨遭牢狱之灾;老舍在“文革”中不堪红卫兵的批斗、侮辱和毒打,投湖身亡。沈从文虽然也遭到批斗,坐喷气式,被流放到湖北咸宁去垦荒,但是毕竟避开了毒打、凌辱和牢狱的厄运。他虽然不时感到压抑和痛苦,但是他毕竟没有感到撕心裂肺或者生离死别的剧痛,也没有陷入绝望的精神折磨。即使他常常受到某些人的嘲笑和干扰,但是还是能够做点事情,生活在文物的天地里,多少令他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沈从文虽然找到了新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园地,但是并不能一下子割断与文学的联系,他和文学还有那种藕断丝连的感觉,他心有不甘。依据理智,他深深懂得:“如果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自己已经定型的写作方式与已经自觉的社会要求之间,必不可少地存在着冲突。”(凌宇:《沈从文传》,第437页。)而且,他还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功夫已经被废了许多,他与文学界的许许多多老朋友一样,1949年以后再也创作不出过去那些精彩的华章,再也不能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然而,沈从文毕竟创造过文学的辉煌,毕竟在文学的天地里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现在要完全割断与其联系,是多么的艰难!因而,在这断与连的两难中作出选择,既十分无奈,又异常痛苦。
沈从文最终还是离开了他曾经奋斗了20多年的文学,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文物整理与研究。然而在1953年他作为美术界的代表出席了第二次文代会。在这次会上,他不仅见到了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而且还见到了最高领导人。意味特别深长的是,毛泽东似乎对他特别关心,不仅询问了他的工作和身体状况,而且还对他说:“你还可以写小说嘛。”(凌宇:《沈从文传》,第441页。)这句话看似关心,然而沈从文听了一定十分心酸。此时,他的文功已经被废了差不多了,还能写出什么作品!即使勉强写出点小说,还能容许发表和出版吗?或许这只是毛泽东的试探,或许这当中还包含着胜利者的得意。沈从文以他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可能已经琢磨出询问所包含的这些十分丰富的内涵,他没有简单地拿其当令箭,表现出兴高采烈,他只“报以微笑,对毛泽东提出的希望却未能作答。”(凌宇:《沈从文传》,第441页。)他一定记忆尤深,就在前不久,他接到了上海开明书店的来信,他被告知:“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凌宇:《沈从文传》,第442页。)残酷的现实已经伤透了沈从文的心,他当然在毛泽东的试探面前保持清醒。
要想彻底割断与文学的联系是很困难的,文学对于沈从文来说就是他的初恋情人,即使离开了她,他也会在内心深处永远保持他的眷念,他也会在心底保持她应有的位置。平时,沈从文或许忙于工作和各种繁杂的事务而无暇眷顾文学,但是当他遇到仍然在坚守文学的老朋友的时候,当他遇到政治气候比较宽松的时候,埋在心底的文学情思一定会浮出水面。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文艺界立即活跃起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编写了《沈从文小说选集》准备出版,当书稿送到沈从文手里的时候,他的内心立即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平日里被深深压在心底的文学情思又涌起波澜。他的胸中燃烧起创作的欲望,他想提笔写作重新回到文学的队伍。但是,不久更加暴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沈从文刚刚燃烧起来的文学激情再次被无情地压制住。
文功被废
这年夏天,沈从文家里来了位自称是青年学生的不速之客,要采访他,并且表示:“你是著名的老作家,解放后对你的待遇太不公平,你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一定代你写出,在报上为你鸣不平。”(凌宇:《沈从文传》,第454页。)这个所谓的青年学生到底怀有什么意图,是不是受人指派来试探他的态度呢?一时搞不清楚。经历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沈从文立即警觉起来,拒绝了他的采访与报道。沈从文只是嘴上表示他自己没有什么不平,其实严酷的现实令他只能将委屈压在心底。从1948年受到郭沫若等人的批判,到一次文代会他被边缘化,从文学期刊不再向他约稿并且拒发他的作品,到开明书店代为焚毁书稿和纸型,沈从文能不感到委屈吗?他的心里怎么会没有不平?但是他更看到1950年以来文艺界一波接一波的大批判运动,特别是胡风和丁玲这样的人物都受到严重迫害,沈从文能不从中吸取教训吗?正是这些惨痛的教训给了沈从文以严重警告,他只能按照当局的意识形态要求去看待问题,发表言论。久而久之,沈从文在自觉不自觉中与当局保持一致。因而他对当局的批判和整人表示赞同,没有表示任何疑义。1956年到1957年的鸣放期间,许多人出于一时冲动或者把持不稳而提了意见,结果遭受迫害。而沈从文则一直不为所动,在这期间一言不发,守口如瓶。他必须将自己隐藏得很深很深,即使要讲话,他也讲些让当局很放心的话,表明自己的驯服和顺从。他说:“我拥护人民的反右派,因为六亿人民都在辛辛苦苦的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决不容许说空话的破坏。如有人问我是什么派时,倒乐意当个新的‘歌德派’,好来赞美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成就。”(李扬:《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第128页。)沈从文的这种表现给最高当局留下了印象,这也正是他们需要的沈从文。而此时的沈从文再也不能写出过去那样的作品,又表现得比较服贴。然而,当局对沈从文的这种表现并不完全满意,还有更高的期待,那就是将他改造成按照其意识形态写作的作家。1961年夏,沈从文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到山东青岛住下,计划以其内兄张鼎和——1936年牺牲的共产党员斗争为题材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然而,由于他“毕竟已经有十余年没写小说了,而这部小说从构思、题材到风格都与沈从文早年的写作方式有着很大的距离。另一方面,尽管沈从文想极力适应时代的要求,但在其内心深处,‘文学’依然是一个极其神圣的所在……”(李扬:《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第158页。)这种既想适应时代,又想保持文学的圣洁的矛盾令他失去了创作自由的心境,结果必然导致他的创作流产。这年年底,沈从文和另外8个人一同被安排到井冈山去体验生活。沈从文虽然离开文坛多年,但是一旦能够重返文坛,他还是很乐意的。他很想通过这次访问、调查和工程,能够创作出一部长篇小说。可是,组织上安排的所谓体验生活,不过是到实地走一遭,很像是旅游观光,他们住的是招待所,并且还有井冈山歌舞团的青年陪同。他们很想与当地的农民谈一谈心,看看他们的实际生活,但是沈从文一行却被尊为上面来的领导,受到格外尊敬和热情接待,根本不可能向沈从文等人敞开心胸说掏心窝的话。可见,经组织这么安排,沈从文等人就像油花一样总是浮在生活之水的表面而不能沉到水的深处,更不用谈融于水中。结果自然是与实际社会的隔膜,最终无功而返,创作长篇小说的计划自然也就化为泡影。井冈山之行,沈从文没有写成长篇小说,倒是创作了五言诗《井冈山之晨》。然而毋庸讳言,沈从文的这首诗已经烙上了非常明显的思想改造的印记,除了“歌德”之外,已经没有什么思想内涵,没有属于他个人的精神与情感,而且缺乏诗的意境和艺术性,与前面提到的《新认识》一样都令人感到诧异:这种拙劣的诗作竟然出自一代文豪沈从文之手!这大概算是沈从文最后在文坛上留下的身影吧。而他的这一身影不客气讲是十分委琐的。等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新时期到来,沈从文已经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了,再加上多年不搞创作,人们看到他的只能是数十年前的文学大师的身影。好在他在文物研究中有惊人的建树,才使他在1949年后的人生放射出光彩。
沈从文文功遭废,追根溯源,就在于他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1920-1940年代,作为京派的代表作家,沈从文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又不认同左翼文艺思想主张。在他的朋友圈子中,既有丁玲、胡也频、李达、巴金等左翼人士,又有邵力子、陈立夫等国民党要人,还有胡适、徐志摩、朱光潜等自由主义人士。他与这些朋友的交往基本上限于私交,很少涉及政治。丁玲于1933年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后,沈从文出于朋友情谊,一方面四处奔走,积极营救;一方面发表文章声援和支持丁玲,但是他不卷入政治,因而他既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参加其他党派,就连30年代初影响盖遍全国的左联成立,他也没有加入,始终保持自己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同样,对于朋友们的政治信仰,沈从文从不干预,并且予以尊重,包容朋友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他明确表示:“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之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的笔。”(凌宇:《沈从文传》,第267页。)他对文学和人生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形成了属于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然而他的这些文学观却不能为许多人所容忍,于是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特别是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严厉批评,然而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尽管如此,左翼作家们总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出发,不能容忍,但是无法从学理上说服沈从文。正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将沈从文的创作推向了辉煌。因为他的创作既不像左翼作家从思想观念出发,怀着极大的功利和实用理性去写作,也不像某些御用文人听从别人的意见,根据别人的要求而写作,他由此获得了许多作家都不曾拥有的精神自由,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到了1940年代后期,随着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日益占据优势,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作家们日渐掌握了文艺话语权,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很不符合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于是受到了清算。他不仅被排到“反动”作家的行列,受到批判,而且他的作品也被扫出了文学市场,他的文学话语权也遭到了剥夺。他的深厚的文学功夫由于不符合新政权的口味和需要就必须被废掉,除非他转变到革命文学方面来。因而,沈从文和许许多多不合时宜的作家一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都面临着创作转型的问题,其中不少作家由于一时没有转过来而陷入精神痛苦之中,他们的创作陷入了空前的危机。那些转型成功的作家不久奉出了新的作品,但是几乎都无法和转型前的作品相媲美,这些过去的大师们如今笔下产生的作品不是十分幼稚,就是非常荒唐,无论是郭沫若、曹禺,还是巴金、艾青、张爱玲,都是如此。还有一些无法实现创作转型的作家便只有从文坛上消失,改行干别的。沈从文就是如此。然而,无论转型还是改行,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们几乎都被废掉了文功,就是在50年代初出走香港的张爱玲在短短的时间内也给废了不少。如果说比较例外的,大概就是无名氏,他以惊人的毅力转向了地下写作,因而还能保持自己的写作姿势,最终于1960年成功地完成了长篇巨著《无名书稿》。
历史终于翻过了这多灾多难的一页。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许多作家获得了精神解放,迎来了创作上的第二个春天。沈从文虽然没有像巴金、艾青等人获得第二次文学生命,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在文物研究方面建立了新的业绩,让自己的生命价值找到了新的实现的渠道。然而作为历史惨痛的一页,决不应该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
2010年7月12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
名人透视041:非主流的张恨水
名人透视040:翻越人生大山的路遥
名人透视039:多维贾平凹
名人透视038:多变章太炎
名人透视037:断绝友情的萧乾
名人透视036:第二种忠诚
名人透视036:邓拓:从宣传家到作家
名人透视035:“刀尖上跳舞”的程树榛
名人透视034:大彻大悟的牛汉
名人透视033: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丁玲
名人透视032:从“弃儿”到香饽饽的王学忠
名人透视031:从怀疑出发的林昭
名人透视030:从“农民诗人”到“向阳”诗人的臧克家
名人透视029:纯真顾城
名人透视028:“纯文学”才女林海音
名人透视027:纯粹文人邵洵美
名人透视026:传统文人柳亚子
名人透视025:冲破规训的顾准
名人透视024:超越意识形态的爱国者
名人透视023:“超现实主义”的艾青
名人透视022:曹禺的自我否定
名人透视021:步入深渊的徐铸成
名人透视020:被压抑的欢呼
名人透视019:被汉奸的刘鹗
名人透视018:不愿忏悔的夏衍
名人透视017:不合时宜的独立自尊
名人透视016:被撕裂的何其芳
名人透视015:美丽的噩梦
名人透视014:不对称的爱情与婚姻
名人透视013:并非浪漫的郭沫若
名人透视012:辫子辜鸿铭
名人透视011:被灼伤的爱情
名人透视010:被“战犯”的胡适
名人透视009:被规训了的浩然
名人透视008:被亲情绑架的朱东润
名人透视007:徐志摩与陆小曼
名人透视006:悲哀余秋雨
名人透视005:挨骂的郑振铎
名人透视004:“历史的误会”的瞿秋白
名人透视003:“宪政迷”梁启超
名人透视002:饱受委屈的端木蕻良
名人透视001:爱情教母琼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