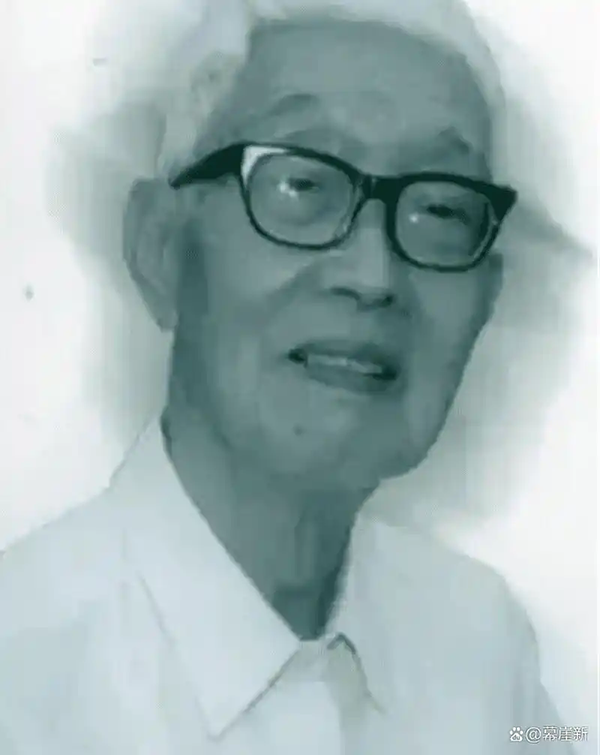
1935年深秋的一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年妇女带着女儿来到了正在莫斯科主编《救国时报》的胡秋原的办公处拜访他。胡秋原先是感到惊诧,后来了解到来向他深表谢意的这位妇女原来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原来,数年前胡秋原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共产党人冯雪峰来访,请胡秋原帮忙给“左联”的一位“病了”的朋友作担保。胡秋原虽然并不知道需要担保的人的真实身份,但是他觉得这个被保的人不是一般的“病人”,应该是共产党方面的要人,然而他没有犹豫,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将其一家安置在不为国民党当局所注意的神州国光社。如果胡秋原是左翼人士或者共产党员,他出面为共产党要人担保,那就是他的责任和义务。不过,真正的左翼人士或者共产党人不会在国民党统治区为自己人担保,因为那样肯定不安全。当时作为无党无派人士的胡秋原能够出面担保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是他还是出面了。而且,如果我们了解到不久之前鲁迅、茅盾、冯雪峰、瞿秋白等人还与胡秋原之间发生过一场激烈的论战,就会觉得胡秋原现在的担保更加可贵。1931年,胡秋原在他主编的《文化评论》的发刊词中自称是“自由人”,声明自己“没有党见”,“站在客观的立场,说明一切批评一切。”(刘炎生:《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05页)随即,胡秋原遭到了谭四海、瞿秋白、冯雪峰(洛扬)等人的围攻式的批评,当然胡秋原也予以反驳。(参见刘炎生:《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第305-316页)然而,论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冯雪峰就来找胡秋原帮忙,而胡秋原则一口应承下来。显然,无论是冯雪峰还是胡秋原,争论归争论,友谊归友谊,激烈的争论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更显得难能可贵的是,胡秋原不计前嫌,不分党派,帮助和搭救共产党人,这不仅显示了他宽阔的胸怀,而且表明他超越了党派意识形态的鸿沟。不仅如此,综观他的一生,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胡秋原就是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伟大的爱国者。
胡秋原并不是天生的意识形态超越者,其实他在年青的时候思想比较激进,十分热衷于政治。早在1924年,年仅14岁的胡秋原随父亲胡康民由黄陂的乡下来到了汉口。他在住处附近的一家书店里惊喜地发现了《新青年》列宁逝世周年与十月革命专号,并且为其中的三个口号——“我们的旗帜——列宁!/我们的武器——列宁主义!/我们的任务——世界革命!”(张漱菡:《胡秋原传》,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5页。本文后面引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所深深吸引。稍后他又买了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对于左倾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正当他思想向着左倾迈进的时候,胡秋原买到了《朱执信全集》,而朱老先生的两句话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将他从奔向马克思主义的途中拉向尼采这一边来。在朱老先生看来:“作人为学自待,应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对社会应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第26页)正是朱老先生的这句话让胡秋原大有醍醐灌顶之感,胡秋原于是转到了尼采研究方面来,很快就成了尼采迷,并且获得了“小超人”的雅号。当然,年青的胡秋原思想并不十分稳定,有时还处于摇摆当中,一旦遇到朋友与同学的影响,他的思想就有了一定的波动。进入武汉大学读书以后,胡秋原遇到了一个名叫严达洙的同学,他对胡秋原进行革命思想启蒙,既向胡秋原推荐漆树芬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等革命书籍,又向他讲解“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第32页)的道理,并且动员胡秋原加入“中学”(指共青团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严达洙的启蒙教育,胡秋原的“脑海中孕育起这样的思想,他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憧憬,也就渐趋认真,所以,当严达洙第二次劝他加入‘中学’(CY)时,他便答应了。”(第33页)此时,我们虽然不能说胡秋原的思想完全被革命的意识形态所控制,但是他的头脑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形态化是毫无疑问的。不久,胡秋原居然根据自己所学到的革命理论,撰写了一篇谈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文章,并且在一家《纪念十月革命专号》上发表。接着,《武汉评论》邀请他参加该刊的编辑工作。而《武汉评论》虽然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但是基本上为国民党的左派与共产党人所控制。
就在胡秋原可能受控于革命意识形态之际,相继发生的两件事情改变了他思想演变的轨道。1926年夏,胡秋原的父亲被人诬陷被捕,差点死于非命。虽然,父亲入狱后40多天被放了出来,但是这让胡秋原感到了政治的险恶,从而厌恶政治。当他遇到董必武等人邀他到省党部工作时,胡秋原没有一口答应,倒是很想推辞,但是又怕伤了情面,因而只好表示要听听父亲的意见。父亲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告诫他:“你不要去参加他们的工作,还是以求学为第一才对。”(第43页)胡秋原的父亲曾经与国民党有些渊源,而且国民党对他还有救命之恩,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民政府既没有“大赦天下”,又没有“免征田赋”,更没有“征求隐逸”,而是整天忙于开会,“闹游行。鼓励工潮,自己扰乱社会秩序”,(第43页)因而他感到非常失望。父亲的话深深地烙在了胡秋原的心上,从而促使他开始疏远党派政治,试图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稍后,胡秋原在武大因反对强迫老教授参加游行示威的事与当时担任武大CP(共产党)书记的同学发生了激烈争执,最后闹翻了脸,胡秋原与曾经对他进行革命思想启蒙的严达洙愤而退场。随后胡秋原退出了CY和国民党组织,从而成为无党派人士。与此同时,胡秋原在他的僻静的宿舍里阅读了《世说新语》以及老、庄、楚辞等古典文学作品,从而产生了避世的心理,试图走进“象牙之塔”。

不过,现代中国给青年知识分子留下的精神空间非常有限,真正的桃花源世界是不存在的,即使有心逃避现实,但是完全超脱现实也是不太可能的。况且,胡秋原并不完全都是受道家文化的影响,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显然还有儒家文化的因子。更何况胡秋原仅仅只是个青年学生,他就是离开了学校,他还是要到社会上谋生,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打交道,怎么可能完全躲进象牙之塔呢?因而,胡秋原虽然对党派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对处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还是十分关心的,或许他父亲遗传给了他关注社会现实的精神。1928年初,胡秋原来到了上海。他本来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的,但是由于他与好友严达洙曾经参加过共青团组织,并且参加《武汉评论》的编辑工作,因而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枪杀与缉捕,胡秋原为此逃到了上海。此时,上海的革命文学在太阳社人士的倡导下正搞得如火如荼,那些革命作家一知道胡秋原来到上海,就动员他加入到革命文学的洪流中来,但是胡秋原表现得比较冷淡。“他根本上就对革命文学不以为然,认为那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如若成功,也只能形成另一个武汉时代的局面,甚至酿成更大的流血事件。”(第65页)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控制胡秋原头脑中增添了理性,他的眼睛也更加明亮,对于事物的判断更加准确。当他读到郭沫若、成仿吾和钱杏邨等人以意识形态作武器攻击鲁迅和茅盾等人的文章时,胡秋原虽然只是个18岁的毛头小伙子,但是挺身而出写文章为鲁迅和茅盾打抱不平,以他的思想理论反对革命文学的那些论调。他在《论革命文学问题》的文章中主张,“艺术并不全是宣传,文艺不是阶级武器……”(第65页)在这里,胡秋原所反对的并不是革命文艺本身,而是意识形态对文艺的奴役,要求文学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而尊重其独立性。1930年,胡秋原因留学费用问题回国,老朋友徐祥霂向他介绍了国内左右两大阵营分别成立的“左联”和掀起的“民族文艺运动”,但是胡秋原只是听着,没有发表意见,因为他此时“对政治不仅绝无兴趣,甚至嫌恶”,他所关心的是“老百姓受苦受难”。(第95页)当他再回到日本时,他偶然结识了新朋友梅龚彬。梅龚彬非常热衷于政治,就政治问题对胡秋原侃侃而谈,胡秋原虽然听得津津有味,但是他并不为其所动。后来又来了王礼锡,胡秋原介绍他们二人相识。而他们俩一个在政治上雄心勃勃,政治抱负不凡;另一个则有“政治癖”,然而胡秋原并不完他们所感染,他“因家庭的痛苦遭遇,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排斥性的淡漠感。”(第103页)当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1920-1940年代出于各种目的趋之若骛投向政治之际,像胡秋原这样跳脱出党派政治,不受意识形态控制实在罕见。既然疏远了党派政治,胡秋原于是将自己的人生定位于学者,他从文艺的起源、性质、发展以及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展开学术研究。尽管他研究这些问题所持的是唯物史观,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他不是那种出于政治功利目的来阐释这些问题,因而他的研究是为了探求真理,具有学术价值,因而没有落入政治的陷阱。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胡秋原比较多地阅读并研究了左倾文艺理论,进而走进了日本人内山所开的书店,广泛接触日本的文艺理论,为了进一步求知,他又去了日本读书。从表面上看,胡秋原在日本接触的主要是具有革命意识形态色彩的左倾文艺理论,但是经过他的思考,他对文艺的理解已经超越了革命意识形态。1930年,胡秋原写成了70万字的文艺论著《唯物史观艺术论》。单看标题,我们很可能将其判断为革命意识形态下的写作,但是在这部著作中胡秋原“不仅肯定了文艺自由,反对所谓‘文艺政策’。同时在思想上也有了一个重心,那便是他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第91页)然而,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往往是对立的,但是胡秋原却将其统一在一起,从而使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党派下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明显的区别。这就是说,胡秋原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当着意识形态看待,而是当着研究问题的方法和理论。因而,胡秋原所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学术意义上的。出于宣传抗战的需要,胡秋原创办了《文化评论》杂志,他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站在“自由的知识阶级”(第126页)立场上写作。虽然他说到了“知识阶级”,但是这个所谓的“阶级”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定义的“阶级”不是一回事,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以地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划分社会群体的。况且,胡秋原所说的“阶级”并没有相应的政党组织,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自由”。这个“自由”是非常可贵的,其意在于不受某个政党和政治集团的控制,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种独立于权力之外的意味。根据这样的思想理念,胡秋原特别主张“文艺自由”,反对“将文艺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反对文艺家做政治集团的“叭儿狗”(第127页),维护文艺和文艺家的尊严。1932年,文化界爆发了一场关于“文艺之阶级性”的论战,胡秋原当初由于沉浸在新婚的甜蜜和幸福之中而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但是他由于在上海文化界已经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而被邀请加入到论战中来。1930年代的中国,虽然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但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左倾的,阶级斗争理论非常盛行,文艺不仅被贴上政治的标签,而且还被要求为阶级斗争服务,沦为阶级搏斗的武器。其实质,当然是文艺的意识形态化。面对文艺的意识形态化的强大势头,胡秋原以深厚的理论功力参与争论,他并不否定文艺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但是他认为文艺并不只具有阶级性,更具有普遍性和人道性,从而将文艺从阶级性的圈套中解脱出来。稍后,胡秋原又发表文章争取言论自由,并且批评左联陈高镛关于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批评。胡秋原的观点当然不能为左翼文人所容忍,于是遭到了瞿秋白、周起应(周扬)、舒月等人的围攻。而胡秋原则以两万三千字的长文《浪费的论争》予以回应。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当时争得面红耳赤,言语中不乏激烈之词,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伤了和气,仍然保持着朋友之情,表现出君子胸怀的坦荡。
胡秋原虽然对左右政治的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但是他非常关系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自从进入中学和大学学习,胡秋原越来越感觉到国家的危机和民族的灾难。1921年,年仅11岁的胡秋原还在读中学,当他了解到国家的危难与韩国亡国的悲惨情形后,他“对日本和韩国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也由此而使他更加自励自勉,努力用功,立志将来为国家而奉献一己的心力,并且立志,不仅绝不做亡国奴,而且要尽力将日本打败。”(第19页)1928年5月,日本侵略者在济南制造流血事件,意在控制中国的青岛与胶济铁路。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慨。有人找到胡秋原约他写一本书揭露“日本侵华的史实和野心”,胡秋原毫不犹豫地应允,而且立即动笔,不到一个月就向约稿人交稿。约稿人接到了书稿还有些不放心,但是当他以挑剔的眼光审读全稿后,不由得表示赞赏。后来上海的大东书局又约他写书,于是他很快又向读者捧出了《近世民族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贯穿他这些著作的思想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忧思。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身在日本的胡秋原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愤慨,他表示决不为了一份官费和文凭而忍气吞声,毅然决定放弃学业,立即回国投入抗战。他深知自己手里没有枪炮,不会打仗,但是他有一支笔,他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笔投入抗战。为了以笔抗战,一向厌恶政治的胡秋原不得不研究政治,然而他与那些政客们大不相同,他不是为了某个集团的政治利益而研究政治,他也不会为政治集团服务,当然不会为政治集团所控制和利用,他认准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他在写作中鼓动抗击日本侵略者,反对不抵抗主义。1932年,日本占领当局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了求和的“塘沽协定”。这一协定的签署引起了国人的义愤,特别是曾经在上海有着英勇抗敌光荣历史的十九路军官兵的严重不满。于是被调到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领导人通电全国要求抗战。身在上海的胡秋原受此感召,在朋友的鼓动下,毅然刊发了陈真如反对“塘沽协定”的演讲稿。这事让胡秋原遇到了麻烦,他在上海安全已经成了问题。这就迫使他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不久,十九路军受中共影响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脱离南京民国政府,胡秋原可能不了解内情,以为是为了抗日,于是参加了这场福建事变。事变之后,南京方面重新控制了福建,于是胡秋原被迫流亡。最初他在香港逗留,但是香港当局也没有容他,限定他出境。陷于困境的胡秋原在朋友的帮助下流亡欧洲。这样,胡秋原轰轰烈烈的政治参与告一段落。就他的这次政治参与,虽然背后有着党派的身影,但是他的出发点并不是为某个党派效劳,而是为了抗日。当时,作为某政治集团的触须胡鄂公虽然以老乡同宗的身份接近他,试图将他拉进其党派时,被胡秋原巧妙地“岔开了话题,也谈些闲事”,很快“起身告辞”(第159页)了。
胡秋原来到欧洲,除了游览欧洲的名胜古迹,参观文化名人的旧居遗迹,博物馆,就是耐心地在图书馆里读书。1934年,胡秋原得到一个机会到苏联旅游。由于苏联所实行的是与包括英、法、中、日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在许多人看来非常神秘,是“‘谜中之谜’的国家”(第212页),就像当今的朝鲜。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确实有不少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到苏联去考察和学习,瞿秋白就曾经到苏联许多地方看了,回来后写了著名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到了苏联,都不可避免地戴上意识形态的眼镜看待苏联的一切,因而他们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产生严重的偏差。从苏联回来后,胡秋原被问到苏联的印象时说:“以我走马观花地观察印象之下,印象最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大’字。”接着他又说:“那个国家实在太大了!那里无涯无际的大森林,还有望不到头的原野,实在大得惊人。我想如果他们真能够努力建设,在学问上、在科技上、还有要在道德方面都能够做得很好的话,以他们的文学成就来推论,其前途倒真是不可限量呢。”(第213页)在这里,胡秋原没有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对苏联作廉价的恭维或浅薄的否定。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苏联的现状。而与他一道去了苏联的王礼锡对于苏联的看法则是直截了当:“这个国家实行共产主义要是成功的话,实在也是很可怕的哟。”(第213页)1934年底,革命作家胡兰畦了解到胡秋原等人的苏联之行,于是来信邀请胡秋原携夫人再赴莫斯科与共产党人一道办刊。胡兰畦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胡秋原已经有所警觉,他不拒与共产党人的合作,但是他不想在合作中失去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因而他在给胡兰畦的回信中就已声明:“你说令友有要事和我‘讨论’,如意见相同,我可以留下,但若意见相左,我即回来。总之,我要求的是来去自由。”(第218页)到了莫斯科,胡秋原受到了王明、康生等人的礼遇,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尽管如此,胡秋原在与王明的谈话中还是明确表示他与共产党人合作的基础,那就是——“我只能在民族抗日的大原则下,写我能写、也愿意写的文章,在这范围之外的,就不是我力所能及了。”(第225页)由此可见,胡秋原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既不是出于个人情谊,也不是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而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的合作。这样的合作显然与党派政治无关。双方合作虽然有过某些不愉快,但是总体上还是顺利的。到了1935年夏,王明等人大概觉得条件成熟了,于是提出要胡秋原加入中共的要求,胡秋原在这个问题上决不含糊,他明确告诉对方:“在我心里,抗日就是一切,其他的事,我没有兴趣。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就是抗日,就是实行民族主义,任何党都应该明白这一点。所以我无意参加任何党派。”(第235页)同时,胡秋原还说:“我一生爱好自由,不喜欢开会,更不愿意受纪律的拘束。”(第235页)虽然胡秋原予以坚决拒绝,但是王明等人仍然不愿放弃,还是在做胡秋原的工作,但是胡秋原声明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自己的思想信念与共产党不一致,并要求离开莫斯科。而王明与康生等人虽然在党内斗争中非常残酷,但是对于胡秋原要求离开,没有为难,他们还分别给胡秋原和他的爱人送了非常珍贵的礼物,以表达他们彼此之间的友谊。1939年4月,作为“重庆行营主任”的张群约胡秋原谈话,要他加入国民党,同样表示谢绝:“谢谢张先生看得起,不过,我只愿意以国民一分子的身份报国,不愿意加入任何党。”他还说:“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拘束。”(第280页)随后,国民党元老、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来找胡秋原邀请他入党,胡秋原仍然没有答应,但是叶楚伧以其真诚打动了胡秋原,同时给他填好了表格,只由他签个字就可以了。而胡秋原在签字之前再一次声明:“我一向认为国家民族高于党,在党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我只承认国家民族而不管什么党了,甚至我只能依照我的良心做事,要是党的决定和我的良心不合,我就照我的意思去做决定。”(第281页)胡秋原的这番话决不是说说而已,他是非常认真的,而且落实在行动上。1942年,胡秋原创办《民主政治》杂志,但是他不是为国民党的政治作宣传,他对支持他办刊的叶溯中阐明了自己的设想:“现在胜利在即望,最重要的是实行民主政治,和平统一,建设国家。”(第299页)随即他在《民主政治》的发刊词中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今后建设中国为一现代的工业国家。保障胜利和工业化的条件,就是巩固统一,实行民主。无统一不能保障民主,无民主不能保持统一。”(第299页)同时,他还强调:“中国之兴衰,不是一党一派的事,也不是各党各派的事,而是全体国民之事。”(第300页)因而,他要将《民主政治》办成一份自由主义杂志。我们知道,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正在为抗战胜利后的一党专政、实行独裁专制制造舆论,大肆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而身为国民党党员的胡秋原居然可以不予理会,呼吁实现民主政治,这不仅表明超越党派政治,不受党派意识形态的约束,而且表现出过人的胆量和气魄与宽广的胸怀。在20世纪的中国,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能有几人呢?
中国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中为战胜日德意轴心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苏联却在侵蚀中国的利益,怂恿和支持外蒙独立,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却为了自身好处而暗地里与苏联达成妥协,牺牲中国利益。面对这样的现实,国内主要的政党或者受意识形态影响,或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于苏美大国的私下里肮脏交易听之任之。在这时刻,胡秋原挺身而出,既揭穿苏美的阴谋,又呼吁国民党当局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签署以承认外蒙独立为主要内容的中苏友好合作条约。早在1943年,胡秋原就以预料到苏联将对中国有所图谋,而且必然从外蒙着手。1945年春,胡秋原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苏联首席代表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与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破例握手是“黄鼠狼向鸡拜年,”苏联人“把中国当孩子”耍,“这大熊必将不利于孺子。”(第303页)1945年夏,胡秋原接到苏联大使馆的一封信,要求赠送全部的《祖国》杂志合订本,由此推断苏联是在试探中国的民意,意在对中国有所图谋。因为苏联大使馆当时已经向中国所有的报刊社索要合订本。胡秋原有了这种不祥的预感,因而向苏联方面提出警告:“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才是促进中苏友好的大道。”(第305页)事实正是如此,略早些时候,苏联、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签订了损害中国利益的秘密协议《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定》。这份秘密协定涉及到中国的外蒙、南满和旅顺等问题,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直到1年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继任总统才把这份密件通知中国政府,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仅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义愤,反而讳莫如深。然而就在1945年夏,国民政府派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到莫斯科参加中苏条约谈判。胡秋原虽然并不知道大国所签定的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的事,但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与苏联大使馆搜集中国报刊杂志的举动推测中国正成为大国争夺利益的牺牲品,现在中苏谈判必然会令中国的利益受损。于是,胡秋原以“卖讲”的形式对全国朝野提出警告,外蒙和南满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接着他又通过接触从苏联返回的中国外交人员了解到宋子文与苏联谈判的内情,进而发现问题确实非常严重:苏联企图割裂中国。危急之中,胡秋原向朝野推出了一份备忘录,大声疾呼:“外蒙断不可失。”(第307页)胡秋原将备忘录通过陈布雷分别提交给蒋介石、宋子文和王世杰等核心人物,但是没有收效,于是他又印发200份《参政员胡秋原对中苏谈判之声明》,呼吁朝野有识之士关注外蒙和南满的严重危机。与此同时,胡秋原还写信给美国驻华大使,严正指出美国牺牲中国利益也必将损害自己的利益——“将使美国子弟流更多之血,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亦不可避免。”(第308页)遗憾的是胡秋原为国家与民族的深深忧虑,并没有让朝野人士有所警醒,从而使他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是他早已作了最坏的打算,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哪怕坐牢也在所不惜。然而,令人非常愤慨的是国民政府没有听取胡秋原的意见,一意孤行,还是与苏联签定了容许外蒙独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签订后的第五天,陷于深深悲愤的胡秋原发表公开信,认为:“从前二十一条,引起全国的反对。如今中苏条约,左右一起叫好,就表示现实主义业已沦浃骨髓了。”(第311页)于是他要反对这种“现实主义”。经受这一次挫折,胡秋原一度产生了退出现实政治的念头。但是他最终没有回避现实,在后来爆发的国共内战中,他表达了反对内战的呼声。到了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胜出,胡秋原了解到自己的言行既为国民党所厌烦,又不为共产党所容忍。他这个超越意识形态的爱国者不知道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究竟何处可以安身,困惑迷茫当中,胡秋原离开大陆经香港去了台湾。到了台湾,胡秋原主要从事文化思想研究,创办《中华杂志》,基本上疏远现实政治。直到1988年9月,他以国民党立法委员身份首访大陆,然而他并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央的授权,而是冒着被开除党籍和判刑坐牢的危险。当然他的大陆之行并不只是个人的探亲访友,而是同大陆领导人会谈,讨论祖国统一问题。他在这次破冰之旅中多次强调:“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团结、统一不可,事不宜迟。”“任何中国人都应该赞成统一。”(第357页)胡秋原的呼声在海峡两岸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因此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第357页)此后的20多年里,两岸关系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统一的道路上并没有迈出关键性的一步,究其原因,窃以为,真正像胡秋原这样超越意识形态的爱国者实在不多,某种意识形态仍然在或明或暗地障碍着国家的统一。
2011年9月11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
名人透视023:“超现实主义”的艾青
名人透视022:曹禺的自我否定
名人透视021:步入深渊的徐铸成
名人透视020:被压抑的欢呼
名人透视019:被汉奸的刘鹗
名人透视018:不愿忏悔的夏衍
名人透视017:不合时宜的独立自尊
名人透视016:被撕裂的何其芳
名人透视015:美丽的噩梦
名人透视014:不对称的爱情与婚姻
名人透视013:并非浪漫的郭沫若
名人透视012:辫子辜鸿铭
名人透视011:被灼伤的爱情
名人透视010:被“战犯”的胡适
名人透视009:被规训了的浩然
名人透视008:被亲情绑架的朱东润
名人透视007:徐志摩与陆小曼
名人透视006:悲哀余秋雨
名人透视005:挨骂的郑振铎
名人透视004:“历史的误会”的瞿秋白
名人透视003:“宪政迷”梁启超
名人透视002:饱受委屈的端木蕻良
名人透视001:爱情教母琼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