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许多革命作家一样,邓拓也是一个令人唏嘘和慨叹的人物。这些作家人生道路基本是早年在激情的推动下,怀着崇高的理想积极投身革命,为了信仰而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为革命工作。可是,他这个忠诚而执着的革命者却不得不离开他所长期从事的革命宣传,走到了文学创作上面上来,然而,像他这样的情况,在文学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呢?又能走出什么样的步伐?这是颇有意味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1912年,邓拓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前清的举人,而且为人正派,由于“对官场的一套格格不入”(庞旸:《邓拓和他的家人》,中国地质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3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而辞官还家,做了教师。按照常理,这应该是邓拓重要的文化基因,不仅涉及到他的脾气性格的形成,而且关乎他后来的人生道路。除此之外,邓拓与许多文化名人一样,少年聪颖,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品德优秀,为他后来成为大家奠定了基础。不过,我们所感兴趣的还是他从一个普通的少年走向革命宣传家的经历。我们注意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经波及到比较偏远的福建福州。当时,名为邓子健的邓拓正在闽侯学校读小学,但是已经目睹了街上的游行集会。到了读中学的时候,邓拓不仅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而且还接触到他父亲收藏的《史的一元论》《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宣言》等革命著作。同时,邓拓在学校里不仅积极参加演讲比赛,而且还和同学们组织起政治性社团“野草社”,自编自印《野草》刊物,发表诗文“抨击时弊,阐述革命理想,自喻在严冬中勇于抗争,以顽强的生命力迎接春天的野草”(第9页)。由此可见,邓拓在青少年时期就已表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他和他的同学们常常议论“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正是这种政治热情决定了他的人生选择。1929年,邓拓高中毕业,来到南京看望他的三哥邓叔群。此时,他的三哥已经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见到弟弟高中毕业很高兴,建议他报考清华大学,将来还可以到国外留学,并且表示弟弟将来“一切读书费用由他承担”(第9页)但是,邓拓没有接受三哥的建议,他到上海投考了光华大学法学系。三哥听到消息后为他没有报考清华感到不解和可惜,邓拓则反问三哥:“你以为上清华和留美才能学到东西吗?才是青年人的正路吗?”(第10页)邓拓的反问单从道理上看是对的,然而他这里隐含的东西则十分明显。邓拓的心目中,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中心”(第10页),他来到这里可以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可以“系统地研读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寻找挽救国家命运的真理”(第10页)。这就是说,邓拓来到上海不是为了长知识与做学问,而是为了他心目中的政治理想。
当时的上海确实有些所谓的大学,不是以学术为根本,而是以革命政治为指导,所培养的也不是学术和社会建设人才,而是政治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邓拓所就读的光华大学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在这里,邓拓“广泛地阅读了一些经济学和哲学名著,选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第11页)在光华大学读了两个学期,邓拓大概觉得不够过瘾,于是转到了上海法政学院继续读书。此间,邓拓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这个简称为“社联”的组织并非字面上所表明的学术团体,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该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在中共党团组织的秘密引导下,配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斗争,发动群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散发标语传单等”(第12页),而且这个组织“非常注重成员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和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严厉驳斥一切非‘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第12页)从这里可以看出,“社联”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排它性和封闭性。当某一思想定于一尊,奉为唯一真理的时候,其封闭性和排他性则显而易见,这不仅拒斥其他一切人类思想和精神财富,而且固步自封,妄自尊大。在这样的组织里,每个人都将失去思想,沦为他人的精神奴隶和斗争工具,无条件地充当别人的夺权炮灰。而且,这些精神奴隶还自以为是,反对一切与其不同的主张和意见,并且想方设法将他人引诱到自己的政治理论上来。如果要追溯邓拓的悲剧根源,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悲剧命运就已注定,即使后来没有被迫害,没有自杀身亡,他也已陷入了一场悲剧,一场导致人类精神疯癫的悲剧。
1931年,邓拓由于“日夜奔波于工厂、学校,组织工人、学生参加斗争”(第13页),并且参加了抗议示威而被捕。他虽然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刑讯,但是没有屈服,从品德上说没有问题,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充当了政治炮灰。后来还是他的三哥邓叔群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将他保释出狱。出狱以后,邓拓仍然陷于政治之中,利用在家调养的时间,阅读了政治理论著作。1933年由于福州城发生了“闽变”(即19路军与蒋介石政府公开决裂事件),邓拓再次受到了通缉。于是,他在大哥邓伯宇的帮助下,进入了河南大学经济系读书。在这个“比较安定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里”(第16页)邓拓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做出了成绩,撰写了近10篇论文和20多万字的被称为“扛鼎之作”(第16页)的《中国救荒史》,在学术上有所长进。如果他安心地致力于学术研究,后来很可能成为令人敬慕的学术大师。然而,很可惜他没有坚持下去。
1935年冬天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再次激发起邓拓的政治热情,他于是放弃了做学问,再次转到政治运动方面来,很快就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且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不久又一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一次,由大嫂活动将他从牢中捞了出来。随后,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气候比较宽松,邓拓便通过共产党便在西安设立的办事处投奔到边区。
来到边区,邓拓本来想“投笔从戎,献身沙场”(第33页),但是由于读过大学,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便被派到创刊不久的《战线》担任编辑,开始了他的宣传生涯。由于表现突出,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刚刚创刊的《抗敌报》(1940年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报社主任。“《抗敌报》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一张三日刊石印小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最早的一份新闻报纸。”(第34页),稍后改为中共晋察冀省委机关报。在中共这里,所有报纸、杂志和后来的广播、电视号称“新闻媒体”,实际上都是宣传工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表面上挂着人民的旗号,那不过是装点门面,哄哄人。其根本目的就是宣传其路线、方针、政策,塑造出中共集体与领导人的光辉形象。这些媒体虽然也有文学和艺术之类的副刊和栏目,其实不过是寓教于乐的宣传手段。与此同时,就是揭露、批判和抨击敌对方的假丑恶。邓拓担任报社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就是“以笔作战”(第36页)。出于宣传的需要,《晋察冀日报》基本上采取的是正面报道,如果没有做到,偶尔偏离这一点,就要检讨“过错”。邓拓不仅兢兢业业,出色地做好宣传报道工作,而且还注意培养一批“宣传干部”(第43页),就同党内第一大笔杆子胡乔木一样,不仅自己要做好宣传工具,还要带动和培养出一大批同类。因此,邓拓所领导的《晋察冀日报》被誉为“一所新型的‘新闻学校’”(第43页)在邓拓的主持下,《晋察冀日报》将刊登国民党官员对于抗战的时局看法的文章视为大忌。邓拓告诫他的同事:“上级规定,这类站在英美立场讲抗战的,不应登载。”(第45页)很显然,这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在他们的心目中,所有的新闻都是站在一定立场上的,而且不是自己(其实是苏俄)的立场,就是欧美的立场,既然欧美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与苏俄的无产阶级立场相对立,因而任何偏离自己立场的东西一概不能刊登。既然立场决定了一切,也就不问别人的言论是否有道理,更不会去问该言论是否有利于人类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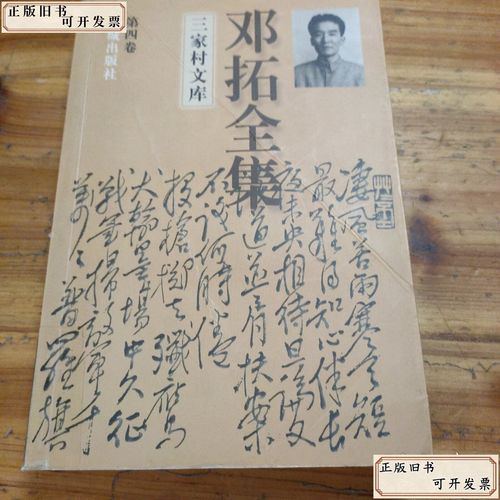
1942年,延安开始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目的是树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让延安升起毛泽东这颗红太阳。作为宣传工具的邓拓当然一马当先。他和他的《晋察冀日报》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宣传者”(第48页)。1942年7月1日,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了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他在社论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发展”(第48页)。邓拓传记作者庞旸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著之一”(第48页)这就是说,邓拓与当年的刘少奇一样都为“红太阳的升起”(高华语)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拓这么做是不是出于和刘少奇一样的目的,我们很难下简单的结论,不过,从他的性格来看,我倾向于出于他的真诚,他的政治激情加上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使他的思想意识忠诚和崇拜最高领袖,他对毛泽东“十分尊敬和钦佩”(第48页)。早在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一文,邓拓读了以后,非常激动:“《论持久战》写得太精辟了!实际、雄辩、逻辑性很强,通篇充满了辩证法,是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武器,要让边区的干部和人民很快都能读到。”(第48页)如果他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蒋百里的有关军事论述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他又该怎么想呢?到了1944年,邓拓担任主编,编辑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他在该著的《编者的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第48页)邓拓为了制造个人崇拜,居然以晋察冀边区的报纸向全党发出号召,对全党提出要求,其实他的行为已经僭越。如果他能穿过历史的迷雾看到20多年的厄运在等着他,他还会这么做吗?他又会怎么想呢?
尽管邓拓表现非常积极,但是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1944年,邓拓和他夫人丁一岚一起进入了党校学习班,随即在这当中插入一个审查干部和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邓拓由于两次被捕过,虽然没有背叛党组织,但是他还是成了审查对象。对于这次遭到自己阵营里的人的审查,邓拓“一向对党忠心耿耿,内心深处不免会有难言的苦涩和惆怅。但他的组织观念很强,在妻子面前总是隐忍自己的心情,从来没有说过牢骚话。”(第71页)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也因家庭成分受到了审查。这是邓拓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也不奇怪。问题是他虽然是一个历史学家(著过《中国救荒史》),在面对历史时“头脑清醒”(第73页),然而在面对现实政治时,他却看不清楚,头脑根本不够“清醒”,他没有看出整风运动与“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实质,没有看清其背后的专制和非人性,可能以为只是个别人执行政策发生了偏差或者个别人的品德不好。既然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他只能感到苦闷,被动地等待将来政策的调整与改正,等待着领袖的英明,将来给受害者以平反,所以在平反之前也只能“隐忍”。“隐忍”之时,他不会想到自己的造神与这场运动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
好在这场运动对他冲击有限,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这看似与他先前的历史学家的身份不符,但是却符合他这个中共党员的逻辑:作为中共党员必须始终维护党的利益,而党的利益从来都不是由全体党员(或者绝大多数党员)确定的,而是由领袖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来确定,并且通过宣传和教育渗透进党员的头脑。所以,党员在党内无论遇到多大的委屈,遭到多大的冤枉,受到多大的伤害,都不能对党组织有任何怨言,都不能动摇对党组织的信任。那么,那些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员就可以利用党和组织的名义,肆无忌惮地迫害其他党员,无情地剥夺其他党员党章规定的权利和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而且,事情过去之后,虽然大家都认为这是“错了”(当然不会认为是犯罪),也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这样,邓拓很快就从“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新的宣传中来。1945年,为了迎接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党校决定编一个剧本配合学习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这个任务就交给了邓拓。作为任务交给作家写作,这大概是中共历史上比较早的。通常来说,作家都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生命体验创作,表达的是作家的思想和情感。但是,中国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即根据主流意识形态对读者和观众进行教化,这样作家所写出东西往往是权力所需要的,为巩固权力服务。邓拓的这次编戏虽然有历史基础,但是与真正的作家创作相去甚远,与其说是文学作品,倒不如说是以艺术形式出现的宣传品。该戏剧虽然可能因为当权者的宠爱和助推而轰动一时,但成为明日黄花是迟早的事。所以,他的这出戏与许多官样文学一样时过境迁,很快为人们所忘却,更不会在文学史或者戏剧史上占有地位。如果不是传记中提及《李自成进京》,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我还真不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一出戏。
由于在造神运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与编写官样戏剧,邓拓于1949年春这个历史转折关头被提拔为《人民日报》社社长,而且,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日报》被确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这就是说,在邓拓领导下,《人民日报》已由华北区报上升为中共中央的喉舌,那么邓拓也就成了第一喉舌。随着喉舌的提升,邓拓渐渐产生了自己的办报思想:“不把报社的主要力量撒出去,就不能了解党的政策在各地执行的情况,《人民日报》就不能起到党的耳目喉舌的作用,就不能改变现在的被动局面。”(第91页)邓拓还真有点务实精神,他从宣传效果出发来思考宣传方式方法的变革,换一句话说,他不仅要及时宣传方针政策,而且还要帮助搜集这些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以便上面督促和纠正,完全替执政者考虑问题。与此同时,邓拓以拼命的精神投入工作,被称为“拼命三郎”(第91页)。“时常亲自提笔写各类文章。他要求记者‘十八般武器样样皆通’,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典范。消息、通讯、散文、评论、诗词,样样都拿得起。20年中,他总计写了几百万字。”(第93页)借用多年来流行的一句话,邓拓该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不过,邓拓主持下的《人民日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能令人满意。而这形势实际上还是政治风头。邓拓虽然信心满满地搞宣传,但是从根本上说他还是一介文人,这就决定了他对于最高领袖的政治意图不能全面而及时的领会,因而他主持的报纸也就不能令权力满意。1956年,领袖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双百方针”。对照这一政治要求,《人民日报》就显得“沉闷、死板,落后于生活,不能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第106页)。于是,在党内笔杆子王胡乔木的指导下,邓拓对《人民日报》进行了改版,并且提出了四条改进措施:“克服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习气,提高评论质量,增加各种体裁的文章,努力改进文风;增加工作问题和学术问题的讨论使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增加新闻和通讯,改进版面安排,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加强编辑部工作,包括加强调查研究,扩大同群众的联系和作者队伍等。”(第106页)邓拓的这四条措施可以说是和稀泥的产物,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然而却也是留下了隐患。从他的身份来看,他的这些举措没有搞清楚最高领袖的意图,从办报的根本来看,他没有抓到报纸存在的根本──客观而及时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只是在技术层面上作些务实性的调整,不能解决办报存在的根本问题。然而,就是这样的改版,也不能让毛泽东满意,“1957年以后,中国当代历史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却很快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第108页)口口声声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的最高领袖居然自食其言,对于人民群众普遍欢迎的报纸很不满意,真是不可理喻。不过,这暗示了邓拓的改版思路完全是文人式的,他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料,搞不清楚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受到批评的邓拓心里一定十分苦恼,而且压力山大。不仅是他,整个报社的所有采编人员几乎都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于是产生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第108页)邓拓的苦恼还在于最高领导层意见不一,以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等人为代表的务实领导人针对1956年以来出现的冒进急躁情绪,提出了反冒进的意见。而毛泽东则提出大跃进的要求,于是发动“反‘反冒进’”。对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见,毛泽东非常不满,特别是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文章,十分恼火,多次对邓拓与《人民日报》提出“严厉的批评”(第110页)。更令邓拓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竟然擅自“改变‘八大’的路线和方针”(第111页),他很为难,不知是按照八大的路线和方针宣传,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宣传。他只感到“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第111页)。问题还不在担子本身的轻重,而在于他常常左右为难,不知执行哪方面指示是好,或者说报纸到底该宣传什么,不该宣传什么。无论怎么样,他都可能犯“错误”。而且在他所造的神的面前,他无论受到怎样的批评和羞辱,都不能辩解,所有的委屈只能闷在心里。这样,邓拓与毛泽东之间因造神而形成的“蜜月时期”(第111页)也就很快结束了。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措辞相当尖锐:“我看你们是专唱反调,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第114页),“是死人办报”(第114页)。到了这地步,邓拓产生了“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第111页)荒唐念头。经过再三权衡,他觉得只能这样,“因为犯了政治错误,主要是根据领导指示犯的,错误就轻得多;如果被认为犯了什么错误,而又没有得到领导同意,那就罪上加罪,像‘反党’这样的帽子就可能被扣到头上。”(第111页)动辄挨训,工作做到这一步,实在可怜,既没有自尊,又没有自由,他可能觉得做好工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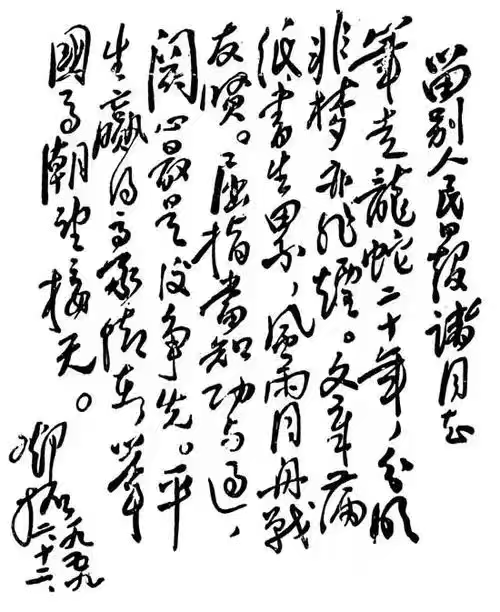
邓拓搞不清楚自己处于这样境地的原因,毛泽东则看得很清楚,批评他是“书生办报”(第114页)。所谓“书生办报”与“政治家办报”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不善于察言观色,猜摩领导人的内心,只根据自己理解和认识去办报,老老实实地宣传自认为是最高层的思想意识;而后者则千方百计地迎合领导的喜好,并且及时根据领导的思想改变而调整自己的认识。既然如此,毛泽东的一次又一次的严厉批评便不可避免。到了这一步,邓拓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向毛泽东请求撤销自己的职务。
1958年8月,邓拓终于调离了《人民日报》,来到北京市委担任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至此,他的宣传生涯告一段落。“邓拓离开《人民日报》社,如释重负,精神上也舒畅多了。”(第128页)不过,邓拓的心情绝不是“舒畅”这么简单,他担任了多年的宣传员,现在黯然离开,一定是五味杂陈,心情十分复杂。好在他很快找到了新的岗位,与文学结缘,搞起了创作。邓拓自幼就对文学感兴趣,而且表现出一定的天赋,在读中学时他就在课堂上按照老师要求作《读罗隐咏蜂七绝有感》。后来他参加革命,虽然忙于宣传工作,但是仍然在闲暇之时写些旧体诗。此时,他离开宣传岗位,一时清闲了,可以拿出许多时间来读书,并且根据读书和思考写些杂感文章。同时,长期在报社工作形成了他的新闻情结和思维惯性,因此他的杂感大多偏重于政论。随着大跃进的严重失败,中共中央对国内政策作了一些调整,政治气候比起两三年前的反右运动时相对宽松。于是一些报刊根据形势需要,对版面作了一些调整,可以发表一些杂文。于是,《北京晚报》邀请邓拓开设杂文专栏,经商定取名为“燕山夜话”。“燕山夜话”由于表达作者的思考,并且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深受读者欢迎,办得“红红火火”(第140页),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便向他约稿,希望开设类似“燕山夜话”的专栏,但是邓拓此时一方面兼职较多,另一方面还得继续给“燕山夜话”写稿,比较忙,于是他就邀请吴晗和廖沫沙加盟一道合办一个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于是,自60年代初以来,邓拓基本上实现了从宣传到文学的转型。不过,他的转型还很有限,还留有非常鲜明的宣传的印记。
邓拓此时的写作,由于正处于政策调整和政治环境的少许宽松时期,所以还能触及到现实社会问题,说了一些真话,批评了一些不良现象,尽管他的这些真话空间与思想空间都十分有限,与鲁迅的嬉笑怒骂和尖刻嘲讽都无法相比,没有游离出主流意识形态,但很可贵,从而为他在当代文学史上奠定了一定的地位。然而,即便是温和的批评,也触犯了某些人,引起了他们的不满。随着最高领导人再次念起了阶级斗争的紧箍咒,极其有限的政策调整不仅中断,而且朝着相反的方向狂奔,“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也都遇到了厄运,相继夭折。与此同时,领导层大搞领袖迷信和个人崇拜,掀起了又一轮造神运动,以便为前不久因大跃进失败而脱落的油彩及时补上。此时的邓拓没有参与这一场造神运动,这不是说他的头脑已经清醒,而是他“对林彪、江青一伙大搞现代迷信,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鼓吹‘天才论’、‘顶峰论’,推行一套庸俗的作法是很反感的。”(第157页)虽然他与毛泽东有了近距离接触,多次受到毛泽东无根据的批评和羞辱,但是他没有对自己当年参与的造神进行反思和检讨,这就决定了他的认识没有根本改变,毛泽东这尊神在他的心目中仍然占据一定的地位,他所反对的只是“庸俗化”。他在同《包头日报》同志的谈话中说得很清楚,对于毛泽东思想“既不能那么玄,又不能贴标签”(第157页),“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形而上学,不要烦琐……不要死扣字眼”(第157-158页)。其实,邓拓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供奉着他心目中的神,所不同的只是造神的形式而已。
即便如此,邓拓在接下来的“文革”中惨遭迫害。他与吴晗、廖沫沙因“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而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江青主持写作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污蔑邓拓‘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第164页),他的《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第146页)。随即,姚文元、关锋等人紧跟而上,纷纷发表文章向邓拓开火。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同日,《红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直接指责邓拓“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第165-166页)面对这样无限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信口雌黄、随口诬陷,邓拓很想“向中央申诉”(第166页),但是谁听他的申诉呢?如果说毛泽东的批评让他感到委屈,他还能够承受,如今对他进行精神“围剿”的则是一批他看不上的家伙,而且还无处诉说和申辩。他的精神一下子垮了,绝望了,他只知道“文化大革命”仅仅开始,漫漫无期,不知道何时才到尽头,而且这是由他心目中高高在上的神所发动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绝望之中,邓拓自杀身亡。
邓拓怎么也没有想到,孜孜追求的革命不仅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造福于天下,而且还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给整个民族造成巨大灾难。许多人为此感到非常困惑。邓拓临死时极度矛盾:一方面,他的心目中供奉的那尊神依然巍然屹立,令他不敢正视;另一方面,历史又是这样的诡秘,现实如此残酷,像他这样忠诚而且驯服的人竟然落到这样的下场,他怎么能想得通。即使他离开令他左右为难的宣传岗位,转到文学方面来,他还是没有被放过。
过了10多年,邓拓得到了平反,有关方面为他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追悼会,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只是他的悲剧是如何产生的,根源何在?不知道能有几人予以反思和检讨,也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人保留下那段惨痛的历史记忆!邓拓在天之灵在得到平反后仅仅感到欣慰和感激?他是否会反思自己的人生迷误与理想错失?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2018年7月24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
名人透视035:“刀尖上跳舞”的程树榛
名人透视034:大彻大悟的牛汉
名人透视033: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丁玲
名人透视032:从“弃儿”到香饽饽的王学忠
名人透视031:从怀疑出发的林昭
名人透视030:从“农民诗人”到“向阳”诗人的臧克家
名人透视029:纯真顾城
名人透视028:“纯文学”才女林海音
名人透视027:纯粹文人邵洵美
名人透视026:传统文人柳亚子
名人透视025:冲破规训的顾准
名人透视024:超越意识形态的爱国者
名人透视023:“超现实主义”的艾青
名人透视022:曹禺的自我否定
名人透视021:步入深渊的徐铸成
名人透视020:被压抑的欢呼
名人透视019:被汉奸的刘鹗
名人透视018:不愿忏悔的夏衍
名人透视017:不合时宜的独立自尊
名人透视016:被撕裂的何其芳
名人透视015:美丽的噩梦
名人透视014:不对称的爱情与婚姻
名人透视013:并非浪漫的郭沫若
名人透视012:辫子辜鸿铭
名人透视011:被灼伤的爱情
名人透视010:被“战犯”的胡适
名人透视009:被规训了的浩然
名人透视008:被亲情绑架的朱东润
名人透视007:徐志摩与陆小曼
名人透视006:悲哀余秋雨
名人透视005:挨骂的郑振铎
名人透视004:“历史的误会”的瞿秋白
名人透视003:“宪政迷”梁启超
名人透视002:饱受委屈的端木蕻良
名人透视001:爱情教母琼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