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被告知,陕北延安是革命圣地,就像北京天安门与根据地井冈山一样,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后来我读了中学,从书本和报刊上了解到,抗战期间,全国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踊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可是历史并不都像过去书本和报刊上所说的那样,就有人在被通知去延安的时候,竟然拒绝了,而且这个人还是追求革命的“左联”作家,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如果读了王毅的《艾芜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版。本文后面引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就不难搞清楚其中的原委。
艾芜最初是想去延安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就把战火烧到了上海。早先负责领导“左联”的周扬在解散“左联”后基本上没有新的工作,于是和艾思奇决定去延安。临行前,周扬把艾芜带到家里,告诉艾芜自己要去延安,激发起艾芜要去延安的愿望,但是周扬没有权力带着艾芜一同前往,只是要艾芜去找夏衍,据称夏衍负责这事,可以批准并作安排。于是,艾芜去找夏衍,但是夏衍对他显得十分冷淡。在夏衍看来,艾芜与茅盾关系不错,还给《中流》写过稿子,因而不能算是自己人或者虽说可以算上自己人却不可靠。其实,艾芜早就加入了“左联”,并且由丁玲“提拔”(第174-175页)为中共党员,参加过“左联”的许多政治活动,而且为此坐过监狱。不仅如此,艾芜1年前还在《文学界》上发表文章,表示赞成包括夏衍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进而得罪了鲁迅及其周边的人。然而,此时的夏衍却将艾芜向外推,认为艾芜是茅盾这一边的人。其实,茅盾并不反对“左联”,就是因为他与鲁迅走得比较近,而且发文章批评过夏衍,结果惹得夏衍不高兴,耿耿于怀。然而这事与艾芜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夏衍就因为这点事冷落艾芜。夏衍见到艾芜来找他请求支持和帮助自己去延安,不是以党的利益为重,而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的恩怨(其实算不上什么恩怨),对艾芜说了句推托的话:“你去找潘汉年。”(第215页)夏衍的态度让艾芜“顿觉寒心”。(第216页)艾芜后来没有去找潘汉年,因为他不认识这个接替冯雪峰刚来上海的潘汉年,即使找到,谁能保证不会像夏衍这样冷淡呢?如果说让艾芜去找茅盾帮忙,他可能觉得没有把握。茅盾确实帮助艾芜发表过文章,但是艾芜在“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中显然没有站到茅盾这一边,因而他的内心还是有一些顾忌的。与此同时,艾芜当时心里还有点想法,他认为,只有自己埋头写作,奉献出作品来,就是在为国家为社会作出贡献,也就对民众有好处。艾芜的看法是对的,但是能够作出判断的话语权并不在普通民众那里,而是在政治化了的知识分子这里。一般的政治人物,此时正忙于战争,与敌对的政治集团作战,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问题,而是将判断交给他们培训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五四期间迫于改变社会现状,接受激进的思想理论,从而在政党的影响下很快政治化了。他们掌握着话语权,从具体政党的利益和需要出发,给某个人的写作作出是否符合国家、民族和民众需要的结论。如果一个人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中国,无论他有多大的本领和创作才干,只要没有借助政治集团的力量,他很快就会被边缘化,被挤出文坛。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张恨水,他的创作虽然颇受市民读者的欢迎,但是在主流文坛上就是没有他的地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承认。或许,艾芜此前虽然加入了“左联”,但是他只是一个基层的盟员,本来就没有什么地位,因而他没有那种别人是否承认的敏感,没有意识到组织承认和肯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艾芜可能大略了解到,去延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是谁想去要去就可以去的,有关方面对去延安的人是有严格控制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得到足够的信任,是不可能被批准去的。艾芜按理来说,应该得到信任,早在丁玲被捕以前,他就被“提拔”为中共党员,就已经是党内同志了,哪有不被信任的道理呢?但是道理归道理,现实是现实。在现实中,艾芜虽然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听从组织上命令,散传单、贴标语,搞飞行集会,但是他只是别人手中的一粒棋子,一颗螺丝钉,从来就没有成为领导的心腹,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信任。就连“左联”领导人周扬都在提防着他。1931年冬,艾芜和沙汀还没有加入“左联”,周扬可以在家里接待他俩。等到他们俩成为“左联”成员时,周扬则对他们关上了自家的大门。直到自己去延安前夕,周扬才在家里再次与艾芜见面。对于敌人应该保持警觉在那个非常时期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如此对待自己所领导的“左联”成员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既然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那么艾芜当然感到自己与这些领导之间隔着一层,那么他要求去延安的愿望也就不会那么强烈。
如果说1937年艾芜还是主动提出去延安的事,那么到了1940年,则是身在延安的周扬向艾芜发出了邀请。当时,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组织上大概觉得艾芜是可以去延安的,于是让周扬发来邀请的电报。艾芜自从认识了李克农,就是受了他的教育,渐渐明白了写作的革命规则:写什么?怎么写?给哪些刊物写?都不能随随便便,应该由革命需要和政治形势来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组织上认为:“艾芜的写作已经变得越来越自觉。”(第230页)这就是说,艾芜的写作距组织的要求越来越近,越来越符合延安领导的口味。于是,延安方面通过艾芜“左联”时的老领导向他发出邀请。论理来说,艾芜得到这个消息应该兴奋与激动才是,但是他高兴不起来。组织上虽然给他作了安排,但是要求他将家人留在国统区,只让他一人前往。这实在让人想不通!组织上是答应给他一笔安家费,帮助解决他的家庭困难,但是让他与妻子儿女分开,而且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区域,着实不近人情。况且,艾芜的妻子王蕾嘉也曾是“左联”作家,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革命工作,有什么不可信任的!想来想去,艾芜觉得让他和家人分离的决定实在太荒唐。于是,他这个革命作家做出了让革命领导想象不到的决定,谢绝延安方面的邀请,坚持留在桂林,与妻儿生活在一起。艾芜的这个决定既显示了他对家庭的强烈的责任感,又表现出他鲜明的个性。而这是周扬等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周扬在革命的队伍里可以绝情地甩掉那个一直爱他,帮他,支持他的妻子吴淑媛,去和苏灵扬结成革命的夫妻,他怎么能理解艾芜对妻儿的认真负责的精神呢!而且,艾芜过去是他手下的一员,竟然没有按照自己的指示办事,又怎么能接受呢?然而,此时的周扬对于艾芜的谢绝总有些鞭长莫及,心底肯定留下芥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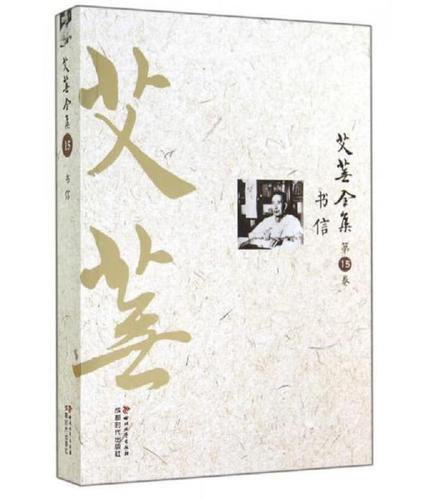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比较紧张,在桂林的亲共文化人处境艰难,组织上号召大家到香港去重建文化基地,以抵制和反抗国民党。但是艾芜这次没有响应。这并不是艾芜故意拒不执行组织上的指示,而是有他的实际困难。他如果要去香港,那么他一家几口人的路费问题没有着落,组织上不能帮助解决,那么依靠个人就很困难。这些年来,艾芜生活在动荡的社会中,况且是一个影响不算大,地位并不高的作家,再加上家庭负担比较重,手头根本没有积蓄,让他一人到哪里去筹措一大笔到香港的路费呢!而且,即使路费能够筹到,但是他到香港以后工作问题如何解决?况且他在10多年前被缅英当局驱逐出境时,也被港英当局登记在案。此时,虽然过了10多年,但是港英当局并没有撤消对他的拘捕令,如果他去香港,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对于艾芜的这些非常实际的困难,组织上究竟是否知道,王毅在《艾芜传》中没有交代。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作为组织,发出一项指示,应该考虑到下级执行者的实际困难,不能以权力强迫别人。然而,在组织这里只有对上级负责,服从命令听指挥,不会考虑接受命令的人的实际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最为难的还是接受命令的人,到底是无条件执行,还是拒绝执行?是非常艰难的选择。如果无条件执行,那如果是小困难,容易克服倒也罢了;如果是无能为力克服的困难,硬要执行,后果不堪设想。艾芜经过一番痛苦的两难选择,最终他选择了婉拒。当然,婉拒也是拒绝,婉拒的是上级,那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然而相权之下,眼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可能被捕的人身自由问题更加严重,更为迫切。因此他只能硬着头皮留在桂林,继续从事自己的创作。颇有意思的是,那些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的文化人到香港转了一圈,很快就回来了。因为他们刚去不久,珍珠港被偷袭,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很快就占领了香港,这些文化人席不暇暖又不得不逃回桂林。可见,就是上级领导未必就有远见,也可能出现情报不准,判断失误的问题。而领导的判断失误,所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结果受累的还是他们的下级。然而,组织号召桂林作家疏散到香港这样折腾人的事,可以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艾芜拒不执行疏散令也不会受到肯定,作为问题说不定暂时放在那里,等待发酵,将来某一天还有算帐的时候。
1944年冬,艾芜一家在生活上陷入了困境,“生活也成了问题,哪里能找到吃的,养活自己和一家人?情形越来越狼狈……”(第252页)许多朋友见到艾芜如此困难,于是给他出主意,建议他到延安去,那里实行供给制,艾芜一家如果去了,至少生活不会成问题。恰在这个时候,周扬从延安托人带来口信,欢迎他带着全家去延安。这次显然与上次不一样,没有将他与家人分开,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案。艾芜表示接受,并且到周公馆去申请,也得到了批准。就在这一计划就要化为实际行动的时候,却节外生枝,出现了一件看上去很不起眼的事,却使这件事泡汤了。艾芜在周公馆申请去延安得到了批准后,在同以群聊天时,以群似乎在开玩笑地对他说:“到了延安,你就不必为一家人的生活发愁了!”(第252页)以群说这句话看似轻飘飘的,而且也符合当时的实际,但是严重伤害了艾芜的自尊——艾芜单纯是为了吃饭去了延安的——而且这话还是出自老朋友之口,艾芜当时虽然没有回击以群,但是他内心的窝火是可以想象的。他觉得自己虽然遇到的困难比较严重,但是自己还是能够解决的,不用到延安去“依靠别人赏给自己饭吃”。(第253页),与此同时,他又想起先前关于去延安而未成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不愉快,进而作出了惊人的决定——不去延安了。随后,艾芜还从重庆市区搬到40里外的乡下居住,专心写作,赚来稿费养家。日子过得虽然非常艰难,但还是过下来了。这一次艾芜拒赴延安,看起来是一句话的小事,但是可以看出艾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强烈的自尊,而这种自尊与他的独立密切相关。从身份来看,艾芜是中共党员,思想倾向革命,但是在骨子里依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自尊。
艾芜,原名汤道耕,他出生时家庭已经破败,但是他的家人在他的名字中寄寓着“耕读传家”的深刻含义。艾芜的身世和名字颇有几分意味:他的家庭的破败表明他不仅人生由社会底层起点,而且几乎一直在社会底层拼搏;他的包含“耕读传家”意义的名字不只是一个符号,而且还是他知识分子身份的标识。作为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员,艾芜不仅饱尝人世间的艰辛,而且形成了他思想倾向革命的基础;他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又使他在思想倾向革命的同时保持着他相对的独立和自尊。艾芜在童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件小事颇有点隐喻的意味。他的父亲要他确定左手和右手,并且给他讲了老半天,但是他就是搞不明白。后来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他虽然偏向于革命的一边,但是他的思想是左还是右似乎也不甚了了。因而,他的人生也就免不了因此而颠簸不已。汤道耕取笔名“艾芜”,也很有趣。他一方面受胡适思想的影响,一方面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胡适曾经提出了“自然主义人生观”,阐述了“小我”——个人和“大我”——人类的问题。受此影响,艾芜便有“爱吾”、“汤爱吾”、“艾芜”与“汤艾芜”等笔名。另一方面,艾芜青少年时还是一个武侠小说迷,其中《七侠五义》中的艾虎就是他崇拜的偶像,那么他这个后来广为人知的笔名“艾芜”原来还与“艾虎”谐音。艾芜这个笔名的含义原来如此丰富,既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侠义精神,又体现现代文化的思想内涵,或者说他的笔名体现了艾芜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精神的融合。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其实笔名同样也如其人,绝不是单纯的区别于他人的符号。后来艾芜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应合着他的笔名,或者说他的笔名印着他的人生底色,而红色则是他所处的时代赋予他的一层色彩而已,只是这色彩比较浓烈,在某些时候遮蔽了他人生的底色,而且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艾芜中学毕业以后,本来是想到北京读大学,无奈他的家庭太贫困,拿不出那么钱。他也想到国外勤工俭学,但是他连从成都到上海的船票都买不起,于是他便踏上了去南方流浪的路途,希望能够到南洋去半工半读。本来他以为凭着自己的年青,走一路混口饭吃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真正踏上路途,他才知道单枪匹马在外面闯荡很不容易。他从四川到云南,再从云南到缅甸,一路含辛茹苦自不用说,但是他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困境,都保持知识分子的身份,无论如何穷困,他都决不颓废、退却和堕落,以自己的坚强意志面对一切险境。这一路流浪让艾芜对社会边缘和底层人们的生活与品性有了充分的认识,让他见识了异域他乡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更让他产生了对于社会底层的强烈认同。因而他从云南到缅甸的行走,决没有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也没有现代绅士的优雅高贵。这种情况下,艾芜一旦遇上左翼思想,很容易与其发生共鸣。所以,当他在缅甸一接触到仰光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就自然而然地投入到其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并且还被派到新加坡参加马(来西亚)共中央召开的党代会。后来,艾芜因参加共产主义小组而被缅甸殖民当局驱逐出境,这样在艾芜的阶级意识中增加了反帝的内容。因而当他到了上海,也就很自然地投入到当时正兴的“左联”的怀抱。
加入“左联”以后,艾芜发现:现实的“左联”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原来他以为“左联”是作家组织,加入以后可以更方便地接触到许多大名鼎鼎的作家,便于文学交流,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创作,但是他发现“左联”小组开会的时候居然“只谈政治,不谈文艺”(第166页)。更令艾芜感到失望的是,“左联根本不谈文艺,也不关心成员写什么作品,发了什么文章”(第167页),他们只要求成员开会听报告,发传单,参加飞行集会,至于盟员的生活问题更是毫不关心,从不过问。可见,“左联”的领导们头脑中只有政治,只有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而那些盟员只是他们听话的工具。他们到了延安,依然如此,没有改变这种思想。而艾芜既然加入了“左联”,而且被丁玲“提拔”为中共党员,成为组织上的人,心里的失望自然不能流露,他只能听从领导的安排。领导传来纸条通知他开会,他就去开会;领导批评他在会上讲话不对,他就立即停止发言;领导要他给“左联”刊物无偿写稿(“左联的刊物,往往都带有突击性质,出几期就总是遭到查封。因此,出版社为了找回自己的损失,无名作家的稿费,往往就被充当了刊物损失的补偿。”(第168页),他就给这些刊物写文章;领导派他到工人子弟学校去寻找和培训工人文艺通讯员,他就去这样的学校教书。艾芜之所以这样俯首帖耳,并不是他有深重的奴性,而是因为他在“左联”内部一直处于低下的地位。但是他到上海,虽然见到了好友沙汀,但是他的根本目的就是想通过写作登上文坛,改变现状,摆脱困境。可是,“左联”并没有给他提供多少机会和实质性的帮助。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并且为贫困所困扰,艾芜难免不产生对于组织的一定的依赖心理。不过,随着在“左联”工作多时,他对其内部的情况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和认识,艾芜渐渐地明白了:原来在“左联”内部,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的都是和他一样没有地位的青年人,而那些文坛大腕是不会跑到大马路上闹革命的,于是他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其实,艾芜在早先就有一些疑虑,对某些问题想不通,而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没有从事政治的那些人的城府,也就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而那些搞政治的人则非常敏感,哪怕只有一丝流露,他都可以觉察到。于是,他在“左联”某些领导人的眼里就成了“小资产阶级”(第168页),是需要改造的对象。而实际上艾芜不仅没有“小资产阶级”的应有的物质条件,而且从来就没有“小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和贪图享受,更没有当时被普遍认为的“动摇”、“软弱”和“温情”。但是,领导们才不管这些,他们只要对某个人看不惯,对某句话或者某件事不满意,就会给对方扣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冯雪峰在一次会议上就是因为艾芜的讲话不合他的意图就打断艾芜的话,批评艾芜的发言“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看法。”(第175页)冯雪峰如此粗暴的工作作风当然引起艾芜的强烈反感,于是他们两人闹翻了。这个矛盾既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组织上的家长式的专制激起了基层成员的不满,其结果不只是个人之间的冲突和关系的恶化,更是组织在基层成员心灵深处投下了阴影。虽然说艾芜不能不在组织内部服从领导,听从指挥,但是领导的权威在他的心底必然要大打折扣。有时,艾芜实在忍耐不住,也会爆发出抗议的声音。他“犟着脖子对顶头上司冯雪峰说道:‘不懂开会的abc,让人家讲完了,你再批评嘛!’”(第175页)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后来,艾芜由于参加“左联”的政治活动而被捕入狱。出狱后,艾芜身体变得非常虚弱,精神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按理说,领导应该在这个时候以组织的名义尽可能给他慰藉和安抚,帮助艾芜渡过难关。但是,从王毅的《艾芜传》的叙述中,我们没有看到哪位领导去慰问和关心艾芜。即使周扬到他家看望,基本上都是谈工作上的事。这多少让艾芜感到心灰意冷,他不再愿意干那些发传单、贴标语、参加飞行集会纯粹政治的事,他要搞创作,既是为了赚取生活费,又是通过创作“参加战斗”,“鼓舞一般青年”(第185页)。艾芜的这个想法是正确而且正当的,但是领导却不这样认为。周扬则认为:“艾芜在对左联的人事安排方面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第186页),胡风则讽刺艾芜是被“吓怕了”,并且暗暗地指斥艾芜:“我只是担心有些人从左面上来,却要从右面下去了。”(第186页)。奇怪的是,冯雪峰和胡风这些人与周扬等人是有严重矛盾和隔阂的,然而在对待艾芜的态度上却走到了一条道上。只是周扬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些。这就是说,在上海的“左联”队伍中,艾芜不仅是个边缘人、底层人,而且还是个两边不受欢迎的人。既然这样,艾芜对于中共党内的这些人就无法亲近起来,他的内心虽然向往革命大家庭,憧憬延安的美好生活,但是他从与这些人相处的关系来看,自己对延安不能不多了一种敬畏。如果说得严重一点,他很可能从自己与这些领导的关系中预感到自己到了延安未必就愉快。
艾芜终究没有去延安,他在上海、桂林和重庆确实吃了不少苦头,经受了生活的磨练。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许正是由于艾芜没有去成延安,他才躲过了延安整风运动与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劫难。那位将他“提拔”为中共党员的丁玲同志不就因为发了《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等作品而受到整顿吗?更严重的还有王实味就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等批评性的文章,结果连脑袋都丢了。他艾芜早年的流浪,历史就很模糊,后来两次被捕过,都可能成为别人整治他的把柄。所以,他没去成延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是幸运的,而这种幸运在于他把握了自己的命运。
1949年新中国成立,艾芜似乎时来运转,居然被推到了官场,成为显赫的官员了。他先是担任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随后又被任命为重庆市文联副主任,接下来他成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不久登上了重庆市文协主席的宝座,继而戴上了重庆市文化局长的乌纱帽。他这个曾经漂泊滇缅,流浪于文坛的作家现在被定为行政十级的官员了。但是,艾芜对于亨通的官运既不兴奋激动,也不感兴趣,他在没有过错也没有受到批评的情况下竟然提出了辞职,这在共产党的干部中几乎可以说绝无仅有。他对自己的辞职作了这样的解释:“我参加了人民政府委员会,争先听见领导的讲话,明白大政方针。至于文化局长一职,一天也没有去办过公。我只想从事文艺写作。……我想起鲁迅说的话:不要做空头文学家,不要把文艺当成启门砖,一进大学教书,就再也不写作品了。”(第270页)艾芜这话确实代表了他的想法,但是这只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对于其他原因,艾芜不好说。表面上看,他的这次辞职与当年拒赴延安似乎有别,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当年在上海,后来在桂林和重庆,艾芜一直与他的顶头上司之间关系比较紧张,中间存在着不小的隔阂,而今即使他进入官场,但是以他的秉性而言,他未必与革命官场的那些人能够和谐相处,历史上的那种紧张关系还可能存在,那么他虽然身在官场,而且获得一定的现实利益,但是他一定觉得受到压抑,心情也不会那么舒畅,既然如此,他或许觉得离开官场可以获得心灵的伸展,这样他提出辞职也就顺理成章了。对于艾芜的辞职,王毅从艾芜“又一次对自己进行身份确认”(第270页)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揭示了艾芜辞职的深层原因,同样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艾芜离开官场,确实如他所说,投入到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中来。他随即去了大型企业鞍钢去“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不久,他还真地向人们献出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以及《夜归》、《剪刀》、《输血》、《雨》、《春天的风》等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不过,艾芜或许还没有意识到,他离开了是非之地的官场,却步入了暗藏地雷的文艺创作的雷区。他当年在上海深受“左联”作家的影响,深受左翼文艺思想的熏陶,思想和创作也很革命,很红色,但是他的那些创作和评论并不能够令当政者满意。1950年,艾芜观看了新歌剧《刘胡兰》以后,感到很激动,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没想到引来了王朝闻、钟惦棐等人毫不客气地批评,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1年以后,重庆《新民报》发表《再生记》,招来了《文艺报》的批评,并且受批评的不只是这篇作品的作者,还包括整个重庆文艺界,而艾芜此时正是文协主席,当然免不了责任。他在新中国创作的最重要作品《百炼成钢》虽然得到一些人的肯定,但是批评的声音也不少。1953年,艾芜从鞍钢返回北京参加第二次文代会。会后,艾芜准备回家乡四川继续“体验生活”并搞创作,但是时任全国作协副主席的邵荃麟则要他留在北京:“作家是用作品教育人民的。但作家也要受教育。你在北京首先可以直接听到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他们都是老的马列主义者,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第287页)邵荃麟的话道出革命“文艺”创作的根本秘密,原来“文艺”创作是否取得成功,不在是否真实反映生活,不在思想的独到深刻,也不在艺术上的创新,而在于是否领会并贯彻领导(袖)的指示和精神。邵荃麟的劝告对艾芜具有非常有效的保护作用,至少可以使他免遭许多批评,少走一些“弯路”,但是从根本上讲则是帮助当局奴化作家,消灭作家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真不知道艾芜是该感谢邵荃麟,还是怨恨邵荃麟。
两年后,艾芜到家乡走了一遭。这一次,他才接触到真正的生活。他住进了家乡的清流乡政府,乡政府出于亲情考虑,让艾芜的两个弟弟汤道安和汤道远来见见分别三十多年的大哥。然而这次见面留给艾芜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亲弟弟已经变成鲁迅笔下的闰土——他们虽然没有像闰土那样喊声“老爷”,但是他们与闰土一样木讷、呆滞——“也许夹杂着对乡政府的敬畏,局促得手脚找不到放处”(第297页)。更令艾芜感到震惊的是他的两个弟弟在老家已经卖了房子,这些年来“都是租借别人的屋子住着,日子过得紧巴。”(第297页)原来,作为工农联盟中的农民的弟弟在新社会里竟然还是如此的双重贫困,与他这个人民作家在近年来的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中所描写和叙述的红红火火与甜美幸福截然不同,也使他的创作顿然失色,苍白无力。然而,艾芜的思想并没有为弟弟的真实处境所引起的心灵震撼所唤醒,也可能是他内心确有某些想法,但是他现在是“人民”作家,他要为“人民”歌唱,必须为“人民”歌唱。他如果将他弟弟的状况真实地书写出来,那他就会被踢出“人民”作家的行列,就可能失去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当然他未必在乎),就可能失去写作的权利和发表的资格(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最终,艾芜经过权衡,还是决定沿着权力指引的创作道路去写作,不久在报刊上发了《千百年来的自然环境改变了——家乡散记》、《统购统销在我的家乡》、《田野在欢乐上笑着——家乡散记》,果然接受了邵荃麟的劝告。
与此同时,艾芜在50年代的政治风潮中跟着当局的节拍跳舞。1951年,艾芜在《文艺报》上发文章,一方面为重庆文艺工作者“呼吸异常自由”(第284页)而欢呼雀跃;另一方面他代表重庆自己表态“文学艺术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服从革命需要”。(王毅:《艾芜传》,第284页)艾芜的这篇文章所说的“自由”显然是谎言,因为它与后面“必须服从”的工具是很矛盾的:当一个人成为别人工具的时候,他就已经交出了自由,沦为权力的奴隶,自由从何谈起!在批胡风运动中,艾芜发表《我从胡风反革命案件中取得的教训》,表示要“去掉自己的自由主义”(第299页)。他在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很可能与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文章的概念差不多,但是其中无疑还包含着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当他去掉这些“自由主义”之后,相信他已经与当局保持一致。在随后的批丁玲的运动中,艾芜将枪口对准了曾经将自己“提拔”为党员的老上级。接着,他发表文章回击右派言论。他将“解放”前后的政治环境作了鲜明的对比:“解放前黑暗的时代,一个文艺工作者,没有任何一点自由,只是在泥泞的路上,痛苦地爬行罢了。……解放后,一个文艺工作者才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像在明朗的天空中,愉快地飞翔一样。”从他本人的实际情况看,“解放”前,艾芜生活确实困难,屡陷困境,但是他的那些作品还是可以发表的,尤其是离开上海以后(在上海期间,他的作品不能发表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没有打入文学圈子);到了“解放”后,艾芜受到了政治的规训,早已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建立了自我审查机制,他在写作之前就已经通过这一机制决定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去写。如果他此时还能够有创作自由的话,他为什么就不能写点东西反映他弟弟真实的生活状况呢?
尽管艾芜努力让自己的言行适应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发展的形势,竭力按照领导的要求去做,但是他还是逃不了劫难。“文革”中,艾芜被指责为“反对革命家鲁迅、围攻鲁迅”的凶手之一,被拉去同“走资派”一起接受批斗。那些红卫兵与造反派们给他扣上了一顶又一顶骇人的大帽子:“30年代围攻鲁迅的黑干将”、“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黑干将”、“文艺黑线派来四川的黑干将”、“神秘的使者”、“国际特务”、“叛徒”等等。到了1968年,他竟然被无辜关进了昭觉寺监狱,由当年的老党员老革命沦为革命的阶下囚。此时的艾芜一定感到非常冤枉,他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当年苦苦追求革命,到头来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到底是他背叛了革命?还是革命背叛了他?他可以向自己追问前一个问题,却不能追问第二个问题。他信仰革命,即使革命发生了变化,与自己早年的追求背道而驰,他也不敢怀疑革命。几乎所有的革命者在这个时候都是这样,即使头脑里闪过这个念头,他也不敢说出来:当年勇敢的革命者而今怯懦了。或许艾芜属于那种不敢怀疑革命的那种。他在“文革”结束以后虽然脑海里盘旋过日本朋友提出的问题:“‘四人帮’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王毅:《艾芜传》,第360页)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答案。而与他同龄的老乡巴金则在《思路》中给出了答案。如果艾芜读到巴金的《思路》,到底是击节称赞呢?还是沉默无语?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修订长篇小说《春天的雾》中捉摸到他思想的一丝脉络:他的人生就是长期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处于底层的他出于改变现状的目的而追赶政治的战车,然而政治的战车却将他总是甩得远远的,他苦苦地追赶,却不幸为其所伤,但是他既然视政治为一种依靠,他就得追下去;另一方面,他的自卑使他在追求政治的过程中不时打量自己,担心自己跟不上政治,于是内心彷徨而犹豫。而革命同样对他是矛盾的,既需要他这样的热情追随者,又要不断地敲打他,伤害他,因为革命绝少对人信任的。而这就造成了艾芜人生的悲剧。
2012年6月13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
名人透视053:荆棘中的独立
名人透视052:交出自由的陈白尘
名人透视051:灰娃的天问
名人透视050:滑入炼狱的乔典运
名人透视049:花瓶冰心
名人透视048:糊涂周作人
名人透视047:好人茅盾
名人透视046:“乖僻”残雪
名人透视045:孤魂萧红
名人透视045:李健吾:书生的政治情结
名人透视044:尴尬沙汀
名人透视043:冯雪峰:浪漫纯真与命运悲剧
名人透视042:废了文功的沈从文
名人透视041:非主流的张恨水
名人透视040:翻越人生大山的路遥
名人透视039:多维贾平凹
名人透视038:多变章太炎
名人透视037:断绝友情的萧乾
名人透视036:第二种忠诚
名人透视036:邓拓:从宣传家到作家
名人透视035:“刀尖上跳舞”的程树榛
名人透视034:大彻大悟的牛汉
名人透视033: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丁玲
名人透视032:从“弃儿”到香饽饽的王学忠
名人透视031:从怀疑出发的林昭
名人透视030:从“农民诗人”到“向阳”诗人的臧克家
名人透视029:纯真顾城
名人透视028:“纯文学”才女林海音
名人透视027:纯粹文人邵洵美
名人透视026:传统文人柳亚子
名人透视025:冲破规训的顾准
名人透视024:超越意识形态的爱国者
名人透视023:“超现实主义”的艾青
名人透视022:曹禺的自我否定
名人透视021:步入深渊的徐铸成
名人透视020:被压抑的欢呼
名人透视019:被汉奸的刘鹗
名人透视018:不愿忏悔的夏衍
名人透视017:不合时宜的独立自尊
名人透视016:被撕裂的何其芳
名人透视015:美丽的噩梦
名人透视014:不对称的爱情与婚姻
名人透视013:并非浪漫的郭沫若
名人透视012:辫子辜鸿铭
名人透视011:被灼伤的爱情
名人透视010:被“战犯”的胡适
名人透视009:被规训了的浩然
名人透视008:被亲情绑架的朱东润
名人透视007:徐志摩与陆小曼
名人透视006:悲哀余秋雨
名人透视005:挨骂的郑振铎
名人透视004:“历史的误会”的瞿秋白
名人透视003:“宪政迷”梁启超
名人透视002:饱受委屈的端木蕻良
名人透视001:爱情教母琼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