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作家柳青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与“十七年”文学联系在一起的。他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与梁斌的《红旗谱》、杨益言、罗广斌的《红岩》、吴强的《红日》并称为“三红一创”,被认为代表着那个时代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而“十七年”文学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了否定,但是仍然具有浓厚的主流政治色彩,因而对于柳青的认识不免和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学挂上钩,情不自禁地把他和贺敬之、魏巍、浩然这些在那个时代走红的作家看作是一类人。因为一般的文学史教材对于柳青及其《创业史》的叙述更是强化了我的这一认识:“小说(指《创业史》──引者)第一部以陕西渭南地区下堡乡的蛤蟆滩为典型环境,围绕梁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展现了合作化运动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教育和团结农民,最终取得了胜利。第二部主要叙述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过程。小说通过对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人物的塑造,回答了农村为什么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作品发表后好评如潮,出版后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就有五十多篇评论文章发表,并围绕着相关问题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讨论。讨论一方面关乎‘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历史道路’,一方面也‘显然带有文学思潮的背景’。”(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158页)然而,最近读了柳青女儿刘可风所写的《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让我认识到了另一个柳青。
刘可风的《柳青传》由三部分构成:“柳青传·上”、“柳青传·下”和“柳青和女儿的谈话”。当我读到第三部分时,我为柳青在1970年代的大胆的,直率的,深刻的谈话所震惊。他在“文革”仍在进行当中所说的那些话让我看到了另一个柳青。早在1970年代初,柳青便以开放的眼光看待美国:“在一段时间里,父亲几乎天天都在谈美国。谈得最多的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说得最多内容的是美国民主制度,宪法的产生过程,两党制的形成,总统的任期,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等等。”(第376页)柳青的这种言论放在改革开放了3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需要一定的胆量,更何况他谈论美国的时候是在“文革”当中,而国家宣传机器正当大张旗鼓地批判美国的政治制度,虽然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中国访问,但是中国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仍然没有改变,而柳青却能够跳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桎梏,客观公正地看待美国的政治制度,肯定其“民主”。这在当时可以算是石破天惊之论。
在1970年代前期,特别是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秦始皇作为法家的代表备受统治者的推崇。最高统治者甚至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举也作为其“丰功伟绩”而大加歌颂。然而,柳青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却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他说:“如果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再延续五百年或一千年,中国在世界上的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它将是发达地区,到不了郑和下西洋,中国人就已经在许多岛上、陆地上繁殖生活起来了。”(第376页)“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杀了有文化、有思想的人,釜底抽薪,想统治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希特勒也是这样。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中国的思想、政治禁锢在极端保守,闭关的范围内,一下子就是两千多年,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的落后地区。”(第376页)柳青的对于历史的认识即使在40年后的今天仍然振聋发聩。在国人思想意识中,“统一”观念特别根深蒂固。然而,柳青则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到秦始皇统一国家的消极作用。柳青的观点未必为人们所接受,但是他的这种对于历史的独特思考与深入研究却意义重大,他早已冲破了意识形态的牢笼,实现了他个人的思想解放。
斯大林在当时中国被认为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并列的革命导师,在“文革”时期更是神圣不可侵犯而受到崇拜。然而,柳青则对斯大林持批判态度。他明确指出:“斯大林违背了列宁精神,是个人独裁。”(第377页)“列宁死后,苏联开始了消灭反对派的斗争,先是组织消灭,随后是肉体消灭。这样的结果,党内民主就变成了掌权者独裁的过场,凡是不同意掌权者的人都宣布为敌人。面对当时党内的政治形势,基洛夫曾建议进行大辩论,被拒绝了。”(第377页)柳青不仅对于斯大林予以质疑和否定,更可贵的是他还将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思考。他以斯大林为镜子来观察眼前的中国,认为:“运动(指‘文革’──引者)能搞成这个样子,是我国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第377页)他甚至大胆地指出:“文革”“是一场空前的浩劫。”(第377页)我们虽然无法判断柳青是否是最早否定“文革”的人,但是他的这些观点在那个时代提出不能不令人敬佩!我们不仅敬佩其勇敢,而且敬佩其思想的敏锐。让人感到可惜的是,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知道的人极少,因而产生的影响极其有限。不过,在那个时代,真正的思想者都遭到无情的遮蔽,顾准、林昭、张志新……莫不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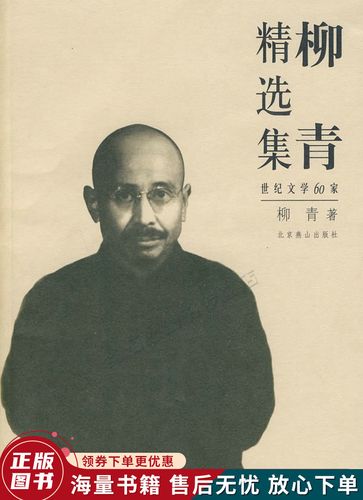
刘可风的《柳青传》所呈现的柳青既有写作《创业史》的那种与极左政治存在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柳青,更有那种敢于说话、善于思考、思想开放的柳青。这两个柳青既相互矛盾、纠结、又在彼此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逻辑。以前,笔者写过《真假丰子恺》(参见孙德喜:《真假丰子恺》,《闲话(十三)苦苦跋涉》,青岛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33-44页)和《双面人老舍》,突出这两位作家人生截然不同的两方面:在丰子恺那里,他一方面真诚地写作,另一方面他制造某种假象来掩护自己的真诚写作;而老舍则一方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又与新政权投桃送李,密切配合。而他一方面被当局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另一方面他又在当局发起的政治运动中惨遭凌辱,进而在痛苦和绝望中投湖自杀身亡。而柳青却表现出的是历史的复杂与诡异,非常值得人们关注。
出生于1916年的柳青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都受到1930年代政治风云的激荡而投入政治。这个时代既承继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文化思潮,又面临着抗日烽火的考验,这就使那一代青年人思想意识和文化性格具有叠层相夹的复杂性。在柳青的思想调色板上,最主要的色彩是红色与粉红色。所谓红色,就是他的投入革命的政治激情;所谓粉红色就是他一直怀有文学梦想,热衷于文学创作。
柳青的政治激情可以追溯到他的家庭出身。柳青,原名刘蕴华,出身于陕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柳青的家庭贫苦,主要不是政治教科书上所说的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而是土匪的抢掠。在一次土匪的抢劫袭击中,柳青那个刚满3岁的哥哥就给土匪一枪打死在母亲的怀抱里,柳青12岁的哥哥在跳墙逃命时被土匪的子弹打穿了手掌,柳青的另一个哥哥手指也被打断,而柳青的父亲则在逃跑时摔伤了腰和腿。这就使柳青的家庭在他出生时就已陷入了困境。因而,他出生时差点夭折,母亲被受到多个孩子严重拖累,担心能否养活,于是试图将他冻死,免得以后受罪,幸亏被奶奶及时发现才没有被弃。当时柳青虽然十分年幼,但是他的童年家庭的困苦多少会在他的心头留下阴影,并且可能产生改变现状的要求。
比较幸运的是,柳青的父亲精明能干,他居然经过多年的努力,扭转了经济状况,家境有了根本好转,从而为柳青兄弟进学校读书,接受良好的教育奠定了经济基础。柳青后来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显然与他开明的父亲供他和大哥读书有关,而大哥又是对青少年时期的柳青影响最大。柳青大哥刘绍华1924年考取北京大学,成为陕北吴堡县的第一个大学生。所以“大哥是蕴华(即柳青──引者)眼中最有学问的人,他崇敬、激动、目不转睛。”(第10页)就在在北大读书期间,刘绍华受到政治的感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把弟弟(指柳青──引者)带进一个革命气氛浓厚的环境中。”(第10页)虽然大哥没有直接将年幼的柳青引上革命的道路,但是柳青却意外地从大哥那里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并且又在刘义维的引领下加入了共青团。不久,柳青的家庭因为柳青的父亲与其叔父发生矛盾,出了人命从而导致“家道中落,一蹶不振。”(第14页)面对家庭的变故,柳青的政治意识更加强烈。数十年后,柳青在长篇小说《创业史》中写下了多年来郁积胸中的愤慨之言:“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第14页)哥哥的影响,再加上周围革命青年的引导与家庭的衰落,柳青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哥哥给柳青的另一重大影响就在于激发起他的读书兴趣,促使他养成爱读书的习惯。柳青本来是一个十分顽皮的孩子,他在幼小的时候,常常“和小伙伴打瓦片、摔跤、捉迷藏、打水仗……”(第8页)进入私塾读书后,柳青是孩子们当中“最贪玩”(第9页)的,“常常领娃娃们戏耍。”(第9页)当柳青到离家30里外的小学读书时,他特别想家,“常常想得眼泪刷刷。”(第9页)后来柳青受到大哥的感召,于是以大哥为榜样,开始认真读书。特别是在家庭遭遇变故之后,父亲已无力承担柳青的读书费用时,是大哥负责解决柳青的上学问题。大哥不仅妥善安排柳青的读书,而且还照顾他的生活,“除了较好的营养条件,生活和治疗上给了蕴华无微不至的照顾。”(第30页)不过,大哥对于柳青的期待是他要学好数理化,将来争取出国留学,后来他还为柳青筹备了出国留学的费用。而柳青在政治上则比大哥走得更远,他的兴趣不在数理化方面,倒是热衷政治。不过,大哥的无私帮助令柳青十分感激。
只是大哥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让柳青感到不解:“大哥为什么变了?和他1928年在米脂县相处的大哥判若云泥。那时,他是个共产党员,也曾积极给工人办夜校,宣传马列主义,组织活动,参加游行,充满理想和热情,期待着光辉灿烂的革命前景……但是,第一次大规模搜捕后,他再次回到北平上大学,就脱离了共产党。”(第33页)大概是柳青当时还比较年青的缘故,不了解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也没有看出党的政策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很不理解哥哥的退出,于是对哥哥有了误解,并且感到可惜。其实,柳青的哥哥一方面看到了党内极左势力的主导导致“盲目行动和过火行动”(第33页),而且还存在着“在革命队伍中一些起于个人仇恨的报复”(第33页)的现象。而大哥则“担心弟弟陷于斗争的漩涡,毁了前程,就想方设法为弟弟铺设了另一条人生的道路。”(第33页)柳青并不理解哥哥的良苦用心,不仅仍然热衷于政治,而且谢绝了哥哥的好意,他在劝说哥哥返回革命队伍无果的情况下差点与哥哥断绝了关系。
柳青虽然一度对政治怀有激情,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文学,仍然表现出对文学的酷爱。只是大哥对此也持反对意见,在大哥看来,“古往今来,文人只有两个下场。一个是饿死,一个是让人整死。”(第34页)大哥的看法是基于历史经验。而柳青则没有接受大哥的意见,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仍然钟情于文学。热爱文学的人与借助文学的人是大不相同的。前者怀有宗教般的情感虔诚地对待文学,将文学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是将文学当作一种利用的工具,为了求得更大的利益,具有极强的功利性。文坛上纵横驰骋的作家很多,大致可分为这两类。徐志摩、戴望舒、朱湘、蒋光慈等人应该属于前者;郭沫若、夏衍、刘白羽、贺敬之、魏巍等人则属于后者,当然也有不少前后发生变化的。就柳青来说,他虽然怀有强烈的政治热情,也一度进入权力场担任一定的官职,但是他的心中一直供奉着缪斯之神,他担任官职不是为了掌握权力谋取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文学创作的便利。这是柳青的纯粹之处,也是他在20世纪中国大环境中没有像一些文人那样迷失自己的重要原因。
通向文学的道路对于柳青来说并不一帆风顺,一方面他在政治的影响下所读的文学作品大多是“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文艺作品”(第37页),这就是说他所读的文艺作品带有很大的政治倾向性好局限性,那么真正经典性的世界文学名著则读得比较少,这就决定着柳青文学营养必然存在很大的偏颇。另一方面,柳青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学创作没有大的长进,令他有些沮丧,觉得自己缺乏文学天赋。好在他没有放弃,只是一度由创作转到了翻译上。柳青后来虽然没有成为文学翻译家,但是他努力学习外语,并且阅读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对他后来的创作与思想的变化还是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同当时许许多多青少年一样,柳青怀着一腔热忱希望改变社会现实,再加上周围革命者的鼓动和帮助,柳青没有按照大哥设计的人生去国外留学,而是为了抗日,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为此他甚至放弃了曾经梦寐以求地进西安临大(由北大、北师大和天津北洋工学院联合创办的临时大学)学习俄文的宝贵机会。1938年,柳青来到了延安。柳青最初的愿望是通过参加革命队伍到前线去抗日,但是组织上看到他有文化,而且喜欢写作,于是将他安排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这虽然有背他的初衷,但是毕竟符合他的文学爱好。然而,组织上的这样安排既有利于柳青在文学创作上有所作为──当然希望他成为革命的宣传员,又可以将他锻炼成革命干部,总之,组织上就是希望他将来为革命多做工作。
而柳青对于组织的安排不仅是坚决地无条件的服从,而且很愿意为党多做工作。说到底,他踏上革命道路完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完全不同于那些政治投机分子,既没想到抓权捞好处,也没考虑到将来的享受。他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共产党身上。然而,柳青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不同于那些浮躁而夸张的空想家。他要以自己脚踏实地的实干将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因而,他要写作,他要搜集素材,他要根据生活实际来写作。因而他人在后方时就经常随剧团下乡演出,以便熟悉生活,后来他如愿以偿到前线去,那里为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感人的写作素材。
柳青既然进入了革命队伍,其思想意识当然会受到延安主流意识形态的熏陶,况且他之前已经读了不少革命理论著作和革命文艺作品。所以,红色思想意识还是在他的脑海里扎下了根。1938年,柳青争取到上前线的机会。在一次战斗结束后,人们知道他念过书,见多识广,于是请他给大家讲点什么。他就给大家讲起了联共党史。“他尽量使用上帝活泼的语言,寻找大家熟悉的实例,深入浅出地解释某些理论。战士们被吸引了。”(第45页)联共党史是斯大林为巩固其党内统治地位而命人编写的一部政治性读物,其根本内容是以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贯穿党史叙述,以强调斯大林的一贯伟大、光荣和正确。柳青此时给人讲授联共党史显然是持诚恳而学习的态度,拜倒在英明领袖脚下。因而,革命队伍所给予柳青的显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柳青后来几十年的人生中,这种血红的色调一直沉淀在他的意识深处,根本没有完全抹去,多少还有些残余存在。更何况柳青的几十年人生基本都是在红色革命的运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度过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柳青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就是他对文学的追求也很实在,在他的性格中似乎缺乏浪漫的情调。这或许与他出身于农民家庭有很大关系。中国农民,特别是贫困落后而封闭地区的农民在长期艰难困苦的生存压力下养成了求实的性格。就柳青来说,他常年病弱的身体使他不能陷入幻想,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所阅读的文学作品以苏俄的为主,而苏俄作品也大多以现实主义为主。所以,柳青刚到延安时,他可没有丁玲、周扬、刘白羽等人那样的豪情壮志和指点江山的气魄,因为他既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到比较发达的城市生活与游览过,他只想踏踏实实地做点事,写出比较满意的作品,进而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作家。而这种务实在柳青的写作初期就有所表现。柳青在有了第一次战地体验后立即写了一篇题为《误会》的小说。“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他刚来部队的一次长途旅行中,既使人感动又令人发笑。”(第45页)但是,这篇小说并没有获得成功,没有产生理想的影响。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柳青又创作了《牺牲者》和《地雷》的小说,他自己还比较满意,但是有人直言不讳地说:“柳青写的文章不行噢!”(第48页),而他自己似乎“也觉得淡而无味”(第48页)。就是到了1949年前后创作的《种谷记》依然存在着“情节沉闷,故事前后不到两个星期,重要人物不多,群众多得叫人记不下”(第103页)的毛病。刘可风毕竟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所以没有细究其原因。我们从“故事是真实的”的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柳青的务实让他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等同起来。他的小说虽然取材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但是他缺乏应有的艺术构思,可能还缺乏应有的艺术想象。这样创作出来的小说怎么能有艺术魅力呢?
不过,求真务实虽然在艺术创作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家的想象,但是可以帮助作家通过踏踏实实地工作为后来的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求真务实可以让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不至于迷失自我,不会跟着风跑。因而,柳青在早期写作未能获得成功之后,他没有气馁,而是坚持读书,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的阅读并不局限在苏俄与革命的文学,而是将眼光推向西欧的巴尔扎克等人,而且他的阅读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浏览,也不是欣赏式阅读,而是深入地研读。“他读书,有时几天停留在意两段文字上,像品酒一样,含在嘴里,久久不往下咽。有时又几十遍从头到尾重读,着迷似的。”(第49页)“他恨不得把所有的文字咬烂,吃到肚子里,全部消化吸收掉。”(第49页)这种踏实地读书让柳青从世界文学名著中吸取到丰富的营养,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不过,由于这是在延安地区,这里虽然有一些西方文学名著,但是毕竟十分有限,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以及思想理论著作,柳青基本上不会接触到,因此他的这种阅读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这就决定了他不会成为世界级文学大师。
正是由于柳青的求实务真,他非常重视基层的生活体验和实践。所以他在延安不愿待在机关里单纯地从事文字工作,而是“急需下到农村去”(第51页)柳青的下乡非常可贵,既不是在领导的号召和要求之下,而是自己的人生选择,又不是短时间的镀金之举,而是成年累月地生活在农民中间。在现当代作家中,与柳青比较接近的大概只有赵树理。他们即使在城里待着,也仍然保持着普通农民的本色与习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柳青完全可以凭借着革命的老资历到城里去享受,将自己的爱人和孩子都可以安顿在城里,让孩子接受优良的教育。但是他却到长安县的落户,他要亲自到王莽村主持那里的刚刚成立的农业合作社工作。当时的柳青由于已经离婚,单身一人。到了长安县,他为了解决自己病弱的身体得到生活照料的问题,于是请当地的领导帮忙给他找对象。他提出的对象条件是“忠厚老实”“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能与他进行思想交流,对他的工作有帮助。”(第114页)这和赵树理与关连中结婚时的情形十分相似。没有考虑爱情,考虑的是工作与生活的便利。当领导介绍的姑娘马葳来到他面前时,他首先向人家提出这样的要求:“同意离开大城市,跟他下乡,做终生住在乡下的准备。”(第114页)
柳青在乡下的生活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作家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他将自己融入到农民之间,当他参与到农村的各项事务中去的时候,他显然已经成为农民的一分子,如果说他与普通农民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比一般的农民接受的教育多一些,认识的字,读过的书多一些,文化程度要高一些,见识更广一些,眼界更开阔一些。但是,他的生活习性与思维方式与一般的农民基本上没有不同。无论是在王莽村,还是在皇甫村,农民的窑洞里,农民劳作的田间,都可见到柳青的身影,而且从他的形态和讲话的方式来看,他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农民形象,与农民作家赵树理一样。
按照当时官方的说法,柳青不仅是“与农民打成了一片”,而且还“扎根农村”,他的思想感情也与农民水乳交融,完全符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的讲话》对作家提出的要求,应该算是代表着这个讲话所指导的方向。但是,他在“文革”中却被揪了出来,沦为斗争的对象,遭到了抄家和批斗,被关进了“牛棚”,他的爱人马葳经受不了残酷的折磨而自杀身亡。柳青的这种遭遇与赵树理十分相似。赵树理也很务实,时刻为农民着想,没有跟着政治运动转,到了“文革”期间被打成黑帮分子同样遭到批斗。更为不幸的是,赵树理竟被活活整死。而赵树理和柳青的遭遇恰恰表明,所谓的“为人民服务”或者“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确实响亮,而且非常激动人心,但是当农民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中被运动,竟而遭到残酷压榨和掠夺而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那些心系农民的干部和作家则一无例外地被当着敌人遭到狠命地整治。倒是那些口口声声要为农民写作而实际上只会忽悠农民的御用文人却格外走红,浩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柳青在“文革”中的遭遇其实早就由他的思想性格埋下了隐患。柳青早年怀揣改变现实的理想投奔革命,这是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他们的理想就是消灭贫困,改变社会不公,推动社会进步,让我们国家富强,不受列强的欺侮,让我们的民族走向现代文明,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根据宣传在心目中按照苏联的样子勾画出一幅未来的图景,革命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第64页),于是他们满怀热情投奔革命,参加革命,乃至献身革命,其精神十分可贵。但是他们没有看到革命的结果到后来竟然背叛了当初的承诺与理想,朝着他们愿望相反的方向而行。而且,这一背叛过程既是渐进的,颇似温水煮青蛙,等人觉察到,为时已晚。况且,能够觉察到的只是少数个体,而推动着革命背叛理想的则是整个集体,这样,那些觉察到不对劲的未必思索到革命理论存在的巨大漏洞,也未必认识到革命者自身的致命缺陷。
有的革命者可能在1920年代就已经觉察到革命队伍存在的问题,红军将领龚楚就是其中之一,他觉得自己无法改变革命内部的政治生态,恐惧遭到肃反运动的政治迫害而不得不逃离革命队伍。而柳青则是到1947年才略有觉察,只是最初的感觉十分模糊,认识也十分肤浅。那是抗战后内战刚打不久,柳青穿越冀东北到晋察冀的封锁线,他在途中遇到了这样的场景:“出村的大道上络绎不绝的农民向敌人方向走去,这是敌我拉锯地区,投向国民党没有多少路。柳青翻身下马,顺着人流,向肩挑手推,拖儿带女的人们盘问,路人带有异样情绪,甚至反感他的询问。”(第92页)这种群体农民投奔国统区的情形令柳青十分震惊。通过了解,柳青得知是前不久共产党进行的土地改革造成的。柳青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显然只停留在政策层面上,根本不会想到这与“解放区”的政治体制之间的联系。他只看到“土改中‘左’的偏向十分严重”(第92页),却没有看到产生这一偏向的根源之所在。其实,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这种偏向就已存在,而且是柳青最早遇到的,但是他当时基本上是在基层工作,而且他的鉴定“第一个被讨论通过”(第53页)。这就是说,那场运动对他没有什么触动,他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不同了,一方面政治运动十分频繁,另一方面政治运动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就连普通农民也深受影响。新中国成立伊始,农村随即进行了土改,不久又搞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最初实行的是自愿的原则,而且柳青也一直坚持这一原则。但是时间不长,农业合作化就由最初的互助组转向高级社,而且上面的政策则是引起农民都加入农业合作社,由原来的自愿变成了强迫,进而引起了农民的不满。1955年秋,柳青所在的长安县就连续发生牲口被害案件,经查是“破坏分子”(第170页)所为。“破坏分子”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与牲口过不去?刘可风在传记中没有交待,但是这种案件“在建社初期全国各地都有发生”(第170页)由此可见,这里的“破坏分子”不会是地主或者富农,而且也不是经过大规模镇压之后漏网的“反革命”及其家属,而是普通的农民,即“贫下中农”。如果是“阶级敌人”,那就不是受到“法律制裁”(第170页)了,而是交由群众进行专政了。普通农民刚刚翻身分了土地,他们应该积极拥护和支持合作社才是,怎么会搞破坏呢?显然是他们被强迫入社,自己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但又没有地方维护自己的利益,才通过“破坏”来发泄心中的愤恨。到了大跃进时期,各地争相“放卫星”,虚报粮食产量,大办食堂,折腾农民,进而不仅伤害了农民,而且在全国还饿死数千万农民。对于损害农民利益,对于折腾农民,柳青渐渐发现了问题,并且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他最初虽然没有怀疑最高层决策的问题,更没有发现造成灾难的体制原因,但是他已经就眼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展开了研究,他以苏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来思考中国的问题。这是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作出的比较切合实际的思考。对于农业合作化本身,柳青没有作深入的思考,由于这是最高领导层的决策,他还不可能怀疑。他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思想理论,竭力探讨符合农村实际的农业合作化的路径。他认为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的“小农意识”(第202页),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目标是让农民“尽快富裕”(第202页),改变农村的贫困落后状况。柳青为农业合作化所设定的目标是对的,他所重视的“小农意识”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是他看重的是集体的力量,而忽视了农民自身的合法权益。柳青推崇集体化的重要依据是民间的一句俗话:“一个人扶十个人扶不起,十个人扶一个人扶起来。”(第65页)这句话是对的,然而现实却是,由于土改,地主和富农都被分了土地和家产,而农民本来就很贫穷,即使分了土地,但是仍然缺少牲口和农具。因此,在建立互助组时,贫穷的农民还是占绝大多数,而条件好的农民大多数不愿意加入互助组,那么所谓“十个人扶一个人扶起来”根本不成立。在建立合作社的过程中,柳青虽然也看到存在着诸如“人心不一”(第121页)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这是农民自身的局限,而没有意识到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农民利益的受损,因此,他在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的过程中,自然以意识形态为指导,一方面竭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一个带领大家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模范人物,另一方面将这一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归咎于农民的“小农意识”和“阶级敌人”的破坏。由此可见,柳青在创作《创业史》时虽然看到了某些问题,但是还没有觉醒,没有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他的创作也就成为那个时代文学与文艺的一种标杆。而1950年代乃至1960年代前期的柳青呈现的就是比较正统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的形象。
不过在这一形象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跟在政治后面跑的柳青,在他的主色调之后,我们还隐约看到某些不协调的杂色。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他渐渐感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从大跃进时期大办食堂,到“四清”运动中王家斌(《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挨整,到上面派来的工作组的工作简单粗暴,再到后来发生了“文革”,柳青以他的务实越来越看到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大跃进运动中,各地根据上面的指示,纷纷办起了食堂。而柳青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总结了“食堂四个‘办不成’”(第220页)。1966年6月底,“文革”刚刚爆发不久,柳青就在家人面前说:“靠这些年轻娃娃就能解决这么大个国家的问题?”(第320页)柳青在红卫兵炙手可热时就已经对其作为提出质疑,而当时全国上下究竟能有几人敢于臧否这些受到“伟大领袖”充分肯定的红卫兵呢?这一问,虽然语气并不强烈,但是分量很重。它表明一个勤于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柳青诞生了。当新的柳青诞生以后,他敢于对“这位国际共产主义领袖(指斯大林──引者)的许多观点持批判态度”(第324页)。新的柳青由于独立思考而头脑渐渐清醒了,当别人热捧样板戏之时,他竟“对‘革命样板戏’有不同看法”(第342),当他被逼对“样板戏”表态时,他回答道:“我从来不看戏,也不懂戏!”(第342页)他没有扭曲自己去迎合,不说假话。到了“文革”后期,有人大肆吹捧“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柳青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把作者都打趴下了。”(第344页)到了1973年,柳青写了一首诗:
落户皇甫志如铁,谋事在人成在天。
灾祸累累无望时,草藁还我有生机。
堆中三载显气节,棚里满年试真金。
儿女侍翁登楼栖,晚年精耕创业田。(第345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柳青不再是对“文革”中某些现象提出质疑,而是对整个“文革”乃至更早些时候的政治运动予以全面否定。他的这首诗写出来之后不是收在抽屉里,而是写成条幅挂了起来。他甚至说:“诗词中说‘到处莺歌燕舞’,这是虚假的,不是从现实中来。”(第419页)如果知道“到处莺歌燕舞”是毛泽东的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的句子,就可以看出,柳青不点名地批评了最高领袖的“虚假”。
作为觉醒者,柳青头脑越来越清醒了。他要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既不屈服于政治压力,在政治运动中“站着过来”,而“不是爬着过来”(第346页),又“决不丧失原则追名逐利”(第349页)。“他不向任何邪恶势力妥协,更谈不到合作了”(第349页)。他坚定表示:“我一生不与任何人结盟,不上任何‘山头’,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艺的。”(第349页)当然,柳青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在行动上。1967年,红得发紫的江青看中了柳青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要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试图拉拢柳青。柳青当然不能公开拒绝,他对朋友说:“我想过,我不表态,我不能上她的船。”(第289页)当时,还有造反派头头拉拢柳青给他写吹捧文章,柳青则表示:“上造反派的船?笑话!我不会拿我三十年党龄开玩笑。”(第286页)他连江青的船都没上,怎么能上一个小小的造反派的船!他的这一人生选择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又抵制了利益的巨大诱惑。从某种意义上说,柳青头脑清醒让自己的心灵获得了一定的自由。
不过,两个柳青毕竟合为一体,而且柳青还是长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之中,他的觉醒是可贵的,同样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反思具有超越时代的一面,也留有环境的痕迹。在柳青看来,农业合作化的目标是正确的,问题出在“走上了错误的路”(第397页),出在“盲动、冒进”(第398页)上,结果“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做了一锅夹生饭。”(第405页)对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柳青首先肯定了它是“人类进步文学的传统”(第454页),问题是,“谈到艺术的部分,特殊性不够”(第454页)没有看到这是政治对文艺提出的严厉要求,更没有看到权力对于文艺的强大干预。对于毛泽东的错误,柳青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看得分明,但是他又说:“毛泽东的出发点大多是为人民的,希望他能醒悟,能认识,能改变。”(第463页)柳青显然忽视了大跃进既然饿死了数千万农民,而毛为什么不予纠正,反而顽固地坚持的问题。如果深入思考这一问题,他或许就能够使自己的认识更加深刻。柳青曾说:“每一个人都受到三个局限性(此句有语病──引者):时代的局限性,也就是社会的局限性;阶级的局限性,也就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局限性;个人的局限性。这三个局限性谁也脱不开,我也不例外。”(第465-466页)柳青在看到现实和历史问题的同时也看到自己的局限。不过,自己的局限到底在哪里?这就很难说了。可惜的是,柳青早在1978年就去世了,如果他能活到1980年代、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他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与反思或许更加深刻,两个柳青或许和谐地合成一体了。
2016年4月23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
名人透视061:“力争跟上时代”的俞平伯
名人透视060:李广田的“遗恨”
名人透视059:“老运动员”公木
名人透视058:浪漫多情郁达夫
名人透视057:快乐王蒙
名人透视056:可敬可鄙的周扬
名人透视055:看啊,天边那片云
名人透视054:拒赴延安的艾芜
名人透视053:荆棘中的独立
名人透视052:交出自由的陈白尘
名人透视051:灰娃的天问
名人透视050:滑入炼狱的乔典运
名人透视049:花瓶冰心
名人透视048:糊涂周作人
名人透视047:好人茅盾
名人透视046:“乖僻”残雪
名人透视045:孤魂萧红
名人透视045:李健吾:书生的政治情结
名人透视044:尴尬沙汀
名人透视043:冯雪峰:浪漫纯真与命运悲剧
名人透视042:废了文功的沈从文
名人透视041:非主流的张恨水
名人透视040:翻越人生大山的路遥
名人透视039:多维贾平凹
名人透视038:多变章太炎
名人透视037:断绝友情的萧乾
名人透视036:第二种忠诚
名人透视036:邓拓:从宣传家到作家
名人透视035:“刀尖上跳舞”的程树榛
名人透视034:大彻大悟的牛汉
名人透视033: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丁玲
名人透视032:从“弃儿”到香饽饽的王学忠
名人透视031:从怀疑出发的林昭
名人透视030:从“农民诗人”到“向阳”诗人的臧克家
名人透视029:纯真顾城
名人透视028:“纯文学”才女林海音
名人透视027:纯粹文人邵洵美
名人透视026:传统文人柳亚子
名人透视025:冲破规训的顾准
名人透视024:超越意识形态的爱国者
名人透视023:“超现实主义”的艾青
名人透视022:曹禺的自我否定
名人透视021:步入深渊的徐铸成
名人透视020:被压抑的欢呼
名人透视019:被汉奸的刘鹗
名人透视018:不愿忏悔的夏衍
名人透视017:不合时宜的独立自尊
名人透视016:被撕裂的何其芳
名人透视015:美丽的噩梦
名人透视014:不对称的爱情与婚姻
名人透视013:并非浪漫的郭沫若
名人透视012:辫子辜鸿铭
名人透视011:被灼伤的爱情
名人透视010:被“战犯”的胡适
名人透视009:被规训了的浩然
名人透视008:被亲情绑架的朱东润
名人透视007:徐志摩与陆小曼
名人透视006:悲哀余秋雨
名人透视005:挨骂的郑振铎
名人透视004:“历史的误会”的瞿秋白
名人透视003:“宪政迷”梁启超
名人透视002:饱受委屈的端木蕻良
名人透视001:爱情教母琼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