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开始意识到,叶橹先生的文学世界,不仅仅属于诗评诗论,他还是一位随笔大家——他作为随笔大家的成就,足以媲美他的诗歌文本批评大师的身份。遗憾的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叶橹作为诗评大家的盛名,仍遮蔽着他作为随笔大家的成就,批评界仍缺乏关注他的随笔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文字,就我个人的阅读范围而言,似乎仅见他的学生孙德喜的一篇《叶橹散文:多重身份的写作》。叶橹先生曾多次对朋友和学生说,你们可以不看我《叶橹文集》里的诗评诗论部分,但可以好好读读第三卷随笔部分。可见他对自己随笔创作的看重。

本文作者与叶橹先生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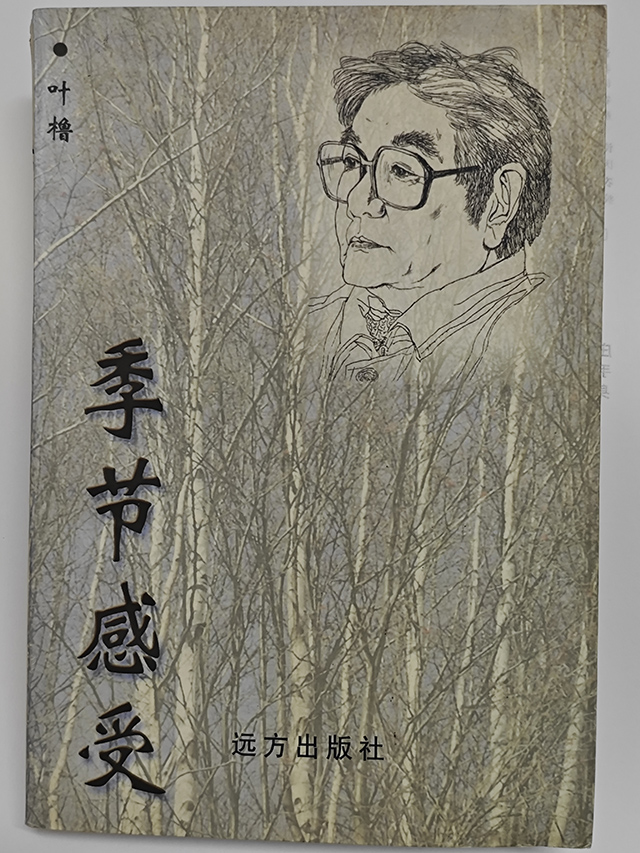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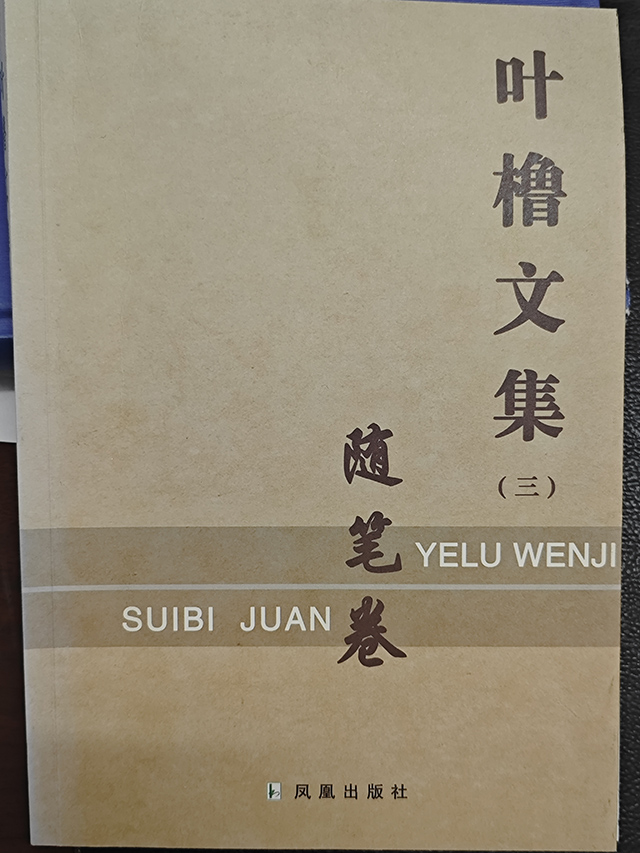
有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学现象,人们对自己的时代往往是看不清晰的。宋人固执地认为,词是诗之余,而后人的评价中,词成了代表宋的文学高峰。明清时,洪应明的《菜根谭》,张潮的《幽梦影》等,被称为所谓清言小品,不入文学的主流——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就是伟大的格言诗集,是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峰之一。当今的人们,认为小说和诗是主流,而我一直异端地认为,在后人的眼中,能够代表今天文学的可能是随笔——那种将思想的力量、思辨的锋锐、诗性的力量熔铸为一体的随笔。如同宋人眼中的词是诗之余,今天的随笔,也几乎是诗人、小说家、学者们的余事,但也正因为是“余事”,它比小说和诗获得了更大的文体自由度,更大的发挥空间。实际上鲁迅先生创作量最大的所谓“杂文”,在文学的意义上称之为随笔更为合适。鲁迅先生本质上是一位诗人,他的《野草》就是伟大的散文诗集,鲁迅先生那些最好的杂文内部,皆燃烧着一团诗的火焰,因而使得他的文字经久耐读,常读常新——鲁迅就是一位随笔大师。
关于当下的随笔,有诗人、作家随笔与学者随笔之说,叶橹先生的随笔,按理可归入学者随笔,但我以为这不够准确。叶橹先生性格率真,喜爱自由与酒,不喜欢系统性的框框条条,这些本就属于诗人的气质,加上他私下里确实写了一些诗,还曾在《诗刊》发表过诗歌,这使得他的随笔风格,置于学者随笔与诗人随笔之间,并获得了两者的优点:学者之风,使他的随笔具有了一种逻辑的力量,苍劲的笔力;而诗人的天性,则使他的随笔时有苏轼所言的佳境,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关于叶橹先生的随笔创作,他在自己的文章《闻风不动思有邪》中有这样一个不够“正统”的说法:
我之所以仍不时地写点东西,是与我的睡眠状态极差有关的。我晚上的睡眠时间,可以用一句“化整为零”来加以描述。能够一次性睡上两个小时,对我就是幸运之至了。总是睡了一个小时左右就醒了,然后胡思乱想一气,再睡;于是反复数次,天就亮了。正是在每次睡眠的间隙中,我的胡思乱想,常常促成我的写作欲望。我虽以写诗评诗论为主,但也不时写点随感之类的短文。这类短文大都是睡不着觉时胡思乱想所致。
叶橹先生的随笔创作,几乎与他的诗评、诗论创作同步,于二十世纪的80年代展笔,跨度迄今已有四十余年。2014年7月,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叶橹文集》,“诗论卷”“诗评卷”“随笔卷”各一本,可见叶橹先生是把他的随笔创作放在与与诗论、诗评等量齐观的位置上的。在这之前的2001年,叶橹先生还专门出版过一本随笔集《季节感受》,38万字。从2014年至今的叶橹随笔,仍分散于各类报刊、杂志,及作者自己的抽屉,尚未成书,好在为他看重的随笔,皆已有所收集。从思想锋芒上来说,叶橹先生随笔创作的黄金时期,应是二十世纪的80年代,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这个时期,从23年的“流放”悲剧中归来的叶橹先生,文字的功力得到了恢复,长期的流放所压抑的情感得到抒发,与自己对时代悲剧的反思,对自己悲剧命运的反思,刚好汇合于一起,促成了一个随笔创作的爆发期。这期间的大部分随笔,堪称鲁迅精神血脉的嫡传,其思想的深度,思维的透澈,触须的敏锐,强大的反思力量,艺术的感染力度,堪与邵燕祥先生的晚年随笔媲美。这些遍布当时各类报刊的随笔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单看其中的一些随笔的题目,如《读书的自由》《尽信与不信》《历史和我们》《清谈误国辨》《愚民》等等,似乎就是从鲁迅的杂文式随笔题目排列而来。叶橹先生的这些随笔中,鲁迅式的思想火花不时闪烁,与那个黄金时期的诗歌一般,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视界。
如《清谈误国辨》一文,由传统的“清谈误国”一说发端,作者认为此说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历史是如此复杂,人们很多时候总是颠倒了事实的因果关系,由此作者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锐见:
大凡一个国家,在它欣欣向荣的上升期,清谈之风是不太可能形成的。清谈之盛行,其实是人们的一种复杂心态的反映。譬如,眼看世风日下,而一些“在野”的平民百姓,手中无权惩治那些贪官污吏,眼看着腐败风气在日复一日地败坏着人们的道德,侵蚀人们的心灵,于是满腔激愤之情无处发泄,只好用清谈的方式来消解自己内心的积郁。这样的清谈,你能说它是误国的吗?
又如《愚民》一文,同样体现了作者深刻的洞察与卓绝的思辨:
愚民一词,主体自然是民,可是冠一愚字,则至少可作两种解释。当愚字作动词用时,显然是愚弄之谓,愚弄老百姓,也就只能是统治者的行为。历来的统治者都希望把平民百姓变成俯首帖耳的顺民,那前提则必须是先愚弄他们。因为有了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乃有大量的愚民产生,于是便有了愚民一词的第二种解释,这里的愚字已经成了形容词……
在对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的层层分析、剖解之后,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柳暗花明又一村”地提出画家兼诗人黄永玉的例子,为“刁民”一词作了平反。黄永玉定居香港后,自称为“湘西老刁民”,作者认为他是经过了彻底的反思和自省之后,才这样给自己加冕的。当顺民做愚民的时间太长了,才知道“刁”的可爱与可贵。
无疑地,叶橹先生的这些文字,有着浓郁的鲁迅味道,称之为鲁迅血脉的嫡传,并不为过。当然,由于这些随笔其深刻的洞察和思辨,往往来自叶橹先生自己坎坷命运的反思,因而别有一番时代赋予的沉重感,以及自己的个人特色。《制造幽默》一文,作者就是以自己的时代经历,对似乎已无新意的“幽默”一词,作了令人抚掌不已的解构与再构。文章由当时正红火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获得灵感,大贪官和珅每次进餐前,都要做出庄严神态,以领唱者的身份口中念念有词:“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紧接着一群妻妾围桌合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再后的场面就具有讽刺意味了,和珅进入为他独设的餐桌,两名侍女轮流为他喂食,真正做到了“食来张口”……作者由和珅的虚伪,联系到自己“流放”期间的一次经历,那时是1968年,正是“三忠于”活动的高潮,作者作为“右派”在南京一街道办的“永红机修组”当工人,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在一次“表忠心”的学习会上,单位的小头头慷慨激昂地带头发言,大意是我们现在能过上这种幸福生活,全靠毛主席老人家的英明领导,所以他对全家人说了,以后在每次吃饭之前,一定要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种虚伪的前后呼应,使文章的幽默感顿生。但文章的令人叫绝之处,是作者指出这些历史上虚伪地制造“幽默”的人物们,有时也会造成自己的“悲剧”。“文革”期间,有带领呼口号者由于精神过于紧张,而把“打倒江渭清”错喊成“打倒江青”,而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作者从潜意识的角度分析,认为这个紧跟潮流的喊口号者,是因为“江青”二字已在他的心理形成了一种“情结”,才会发生这种在局外人看来幽默意味十足的事情。但作者接着又煞有介事的推理到,如果此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竟在“平反”时宣称自己当年的行为是“有意为之”的革命行动,岂不制造了一个更大的幽默!《制造幽默》一文就这样在对传统幽默的层层解构中,实际上将文章写成了一种颇有后现代意味的大幽默剧。
而将自己的人生苦难,坎坷经历,作为随笔创作的推力,最终抵达一种生命的大境界的,是在叶橹先生的晚年随笔创作中,其中的一篇《阅读天空和大地》,堪称不可多得的随笔杰作。如果说,叶橹先生的早期随笔,更多的是一种鲁迅杂文风格的短制,匕首寒光闪烁,而到了后期,尤其是年逾七旬之后,因为年岁的增长,生命的不断觉醒,超越,可以使他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审视自己过去的苦难岁月,因而他晚期的随笔创作虽没有过去的多产,每篇的包容量却愈来愈大,显示出一种沉雄之风。而且,他晚期的随笔创作,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考虑报刊发表的字数限制,现在,他完全是为自己的生命而写作,为了给自己坎坷的一生有所交代而写作,可以放任自己的笔端自由地驰骋为大篇,在往事与苦难、沉痛与反思中,将自己的生命推向最终的大彻大悟。三千余字的《阅读天空和大地》,不仅是叶橹晚期随笔的代表作,整篇文字所呈现出来的沉郁,博大,厚重,甚至令人联想到俄罗斯伟大作家们关于苦难的书写,是配得上作者自己及中国那个时代苦难的杰作。
《阅读天空和大地》这篇随笔,是叶橹对自己过去23年“流放”岁月沉思的结晶:1957年7月被打成右派;1959年——1966年在湖北矿山、农场劳动;1966年5月回到南京,在街道劳动;1969年12月下放江苏灌南农村;1971年落户江苏高邮农村;1976年——1980年在江苏高邮县城“搬运公司”劳动;1980年3月落实政策……这打成右派、劳改、流放的时间,加起来约23年。文中提及,一次一位朋友在跟叶橹闲聊时问:“这23年你没有书读,为什么你后来还能教书写书?”叶橹灵机一动,颇有些激动地回答:“我没有读书,但是我阅读了23年的天空和大地。”这看似轻松甚至有些幽默的回答里,所包含的肉体的折磨、精神的荒凉其实是令人颤栗的,我们不妨对照一下俄罗斯诗人作家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年西伯利亚流放,至少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反思,有《福音书》相伴,甚至可以潦草地写下一些笔记,成为名著《死屋手记》的基础;曼德尔斯塔姆的流放沃洛涅日,此间他的诗歌创作却进入了一个高产期,他在三个笔记本上写满了诗,在诗中拓展了土地与命运的新向度……而叶橹先生的23年劳改,流放,拖板车等苦役之外的时间,就是孤独,隔离,被迫不断地清空自己的精神世界,以至于23年后,他被新时代的命运推到大学讲台上,竟不知如何在黑板上书写。叶橹先生所谓的“阅读天空”,得之于他晚年的诗性“觉悟”,而当初的具体情景,他在文中是这样叙写的:
人所共知,牢房是没有窗户的。它只在门上有一个小洞,以供光线进入和外面巡警在外能够看到屋内犯人的情况。犯人只能席地而坐,不能擅自起立活动。只能需要“方便”时大声向巡警“报告”,经批准后才可“行便”。于是对犯人来说,除从门上的小洞向外窥视,就只有闭目默想了。这时候我才逐渐知道,要想仰望一下天空是有多么的不易。因为除了每天早上半小时的“放风”我们是见不着天空的……
由此若干年后,叶橹先生读到台湾诗人商禽的那首《长颈鹿》,写牢房中的人因仰望岁月而使颈项成为“长颈鹿”的超现实幻觉时,不禁回忆起自己的牢狱经历,而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这篇随笔中最令人痛心的一个场景,是写作者刑满之后的1962年,以“留场就业”的身份转移到黄湖农场,被分配去拾牛粪。拾牛粪的定额必须每天完成,否则不能休息。这一天上午,叶橹只捡了半担牛粪,突然见不远处有一头牛在排泄,便兴冲冲地就要去拾。谁知放牛的小孩认定叶橹是“阶级敌人”,怎么也不让拾,还抓住叶橹拾牛粪的铁扒,说就是不让你们劳改犯拾。拉拉扯扯间,叶橹不禁怒从心起,打了小孩一巴掌后,匆匆逃走了,已经拾好的半担牛粪也不要了……漂泊的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面对的是一群调皮的孩童,抱了他茅屋上飘落下的一些茅草,匆匆躲入竹林,只是欺负他“老无力”,以至于杜甫尚有余兴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而叶橹所面对的这个时代造就的“勇敢”的小孩,是把流放的叶橹当作了阶级敌人,要压倒他。年轻的叶橹打了小孩一巴掌后,却是自己匆匆逃走了——留给他的只有一辈子的痛,烙在晚年的随笔里。
哲人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当然,今天的诗人们仍在写诗,但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诗了。或许同样可以说,自叶橹写下随笔《阅读天空和大地》之后,阅读天空和大地这一姿态,已不再属于传统的诗意,而是注入了历史的沉重与新的内涵,必须换一种解读方式了。
作为一位随笔大家,叶橹先生随笔创作的内容是丰富的,形式是多样的,除了给人印象深刻的鲁迅式的“横眉冷目”之外,他还有大量可归于“闲适”类的随笔,《叶橹文集》第三卷“随笔集”中的“心象景观”辑,基本属于这样的文字,单看那些随笔的标题,如《怀念石榴树》《初识水网》《那年明月夜》《烧老鹅》《无梦不成眠》等等,即感“闲适”之气扑面而来。但叶橹的“闲适”,不同于梁实秋的那种以趣味性为主的闲适,叶橹的“闲适”,往往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看似寻常的事与物,寻到一种新的视角,再通过层层思辨,最终达到一种生命的“觉悟”。应该说,这样“闲适”的随笔实际上是诗性的,属于着更高的层次。
我个人认为,叶橹先生写于耄耋之年的随笔《闻风不动思有邪》,可谓这类闲适随笔的代表作之一,在看似闲适、轻松、从容的笔法下,透出的是一种深层生命的感悟。作者告诉我们,“闻风”的灵感,是从洛夫的诗《因为风的缘故》和徐志摩的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向哪一个方向吹》而来,因为这两首诗都透着一种人生无常、命运莫测的气息,令作者感怀。但作者随即强调,更能引起他内心深处共鸣的,还是曾卓的那首《悬崖边的树》,以及其中的诗句“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这两行诗句,仿佛就是为叶橹的生命与命运而写照。接着作者由“风”的种种隐喻,联想到曾经的那个时代的口号“闻风而动”。由于“闻风而动”这种盲目地紧跟潮流,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无数的苦难,作者指出,人既号称万物之灵长,为什么不能在“风”面前坚定一次,做到“闻风不动”,而坚守住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人格。至于“思有邪”,则是作者与孔老夫子有意开的一个玩笑,孔老夫子说,诗三百一言蔽之曰“思无邪”。作者不由疑问到,“诗三百”中的一些诗,真的是“思无邪”吗?认为孔老夫子是有点故意地实行着“以偏概全”的谋略来维护其正统观点罢了。而从人的实际生活状态来看,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无时无刻都“思无邪”呢?恐怕没有,因此作者认为,“思有邪”才是一种“情理之中”的应有的现象。由此作者得到了一句“闻风不动思有邪”,颇有格言风采,又极富诗性张力。自爱不已的作者便请洛夫等诗人书法家将此格言写成书法,以作闲时欣赏,引出了一系列文坛趣事。更具意味的一次,是诗人林莽书写此格言时,有意将“闻”字改成“文”字,成了“文风不动思有邪”,而有了新的意味,而随笔亦由此宕开新境。
叶橹先生的随笔世界中,还有一些别开生面、不拘一格的创作,如《〈皇帝的新衣〉三题》,在安徒生童话的基础上,做了现代性的继续发展,叙述了那个讲真话的孩子长大以后几种可能出现的局面,以一种解构的手法,将人性的阴暗,人类的悲哀,置于一种极为荒诞的境地。又如《世说新篇》中的18则,是随感,寓言,乃至微小说在文体边缘的一种融合,创造,在对时代弊病的折射、影射中,显示了叶橹作为思想者的风范。这些新世说皆不长,且录其中一则《鼠的权变》如下:
老鼠在过街时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它回到自己阴暗的洞窟之后,想:人们之所以那么恨我,不过是因为我小偷小摸,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做了些手脚而已。如果我变成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出入,或许人们就会对我另眼相看了。
于是,它经过一番乔装打扮,请狐狸先生为它整容,把三角眼修整得圆滑美观些,还配上一副眼镜以改变“鼠目寸光”的毛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它又到时装店购置了高级服装、礼帽、皮手套,像个“人”样了。
从此,它不再处处躲着人们。岂但不躲,而且还一付趾高气扬的样子。有一次它走过猫的面前,猫竟然对它视而不见。起初它还有点胆怯,可是看到猫无动于衷,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猫只是对那一股鼠臊的气味嗅了嗅,感到一阵迷惑,终于又闭了眼睛打瞌睡了。
老鼠终于明白了,光天化日之下干坏事,要比在阴暗的角落里小偷小摸更加方便而显光明正大。不过,首先得打扮得像个“人”样。
发表于2018年第四辑《诗探索》的叶橹先生访谈录中,在谈及自己的诗论诗评写作时,他曾有这样的自述:“我写文章从来不打草稿,都是大体的思路先定下来,然后一气呵成。这样的写作过程中,总有灵感光顾我,我也会发挥得非常好。我也曾试过打草稿,但往往拘谨了思路的自由发挥,效果并不理想。”叶橹先生的诗论诗评的夫子自道,其实与苏轼所言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作文之道是相通的,这使得他在不经意间,将一些诗论诗评写成了极好的随笔。他的诗论,尤其是诗评,往往是他作为一个诗性批评家与所评诗人之间的心灵对话,不时闪耀着撞击的火花——而由这些火花构成的评论,自然是极好的随笔。
其实,把评论当作极好的随笔来阅读,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瓦雷里、奥顿、布罗茨基、帕斯等大诗人的一些诗论诗评,就收入了他们的随笔集中,甚而比他们的诗歌更受欢迎。而大哲学家叔本华、大学者罗兰·巴特的许多文章,也是被世人当作深邃的随笔来阅读的。因而,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将诗评大家叶橹先生的部分诗评诗论当作随笔来阅读,不仅是合理之举,亦呈现了叶橹先生随笔创作的多面性。叶橹先生诗评中的《解读<慈航>》《论洛夫的禅诗》等,诗论中的《第三只眼与第六感官》《呼唤长诗杰作》等,皆可以同时当作极好的随笔来阅读,并由此而更为全面地、丰厚地为一个名“叶橹”的杰出生命存照。
2025年12月19日
相关链接:
庄晓明:我的写作,终会获得应有的“回声”
庄晓明:叶橹论
庄子词典(节选)
庄晓明《庄子词典》:诗意的智慧之花
诗性建构下的人类镜像:评庄晓明《东乡笔记:魔幻,传说,寓言》
庄晓明著《东乡笔记:魔幻,传说,寓言》:东乡诗性建构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