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清源教授积数年之功编撰而成的《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史》(以下简称《学科史》),无疑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时值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简称“河大中文”)设立百年之际,这部逾六百页的煌煌巨著不仅是对一个学科百年沧桑历程的系统梳理与忠实记录,更是一部折射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知识分子命运以及学科学术演进的微观史诗。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学史研究的学者,捧读此书,感慨良多。它不仅填补了区域学科史研究的重要空白,其翔实的史料、严谨的结构和深沉的史识,亦为同类研究树立了新的标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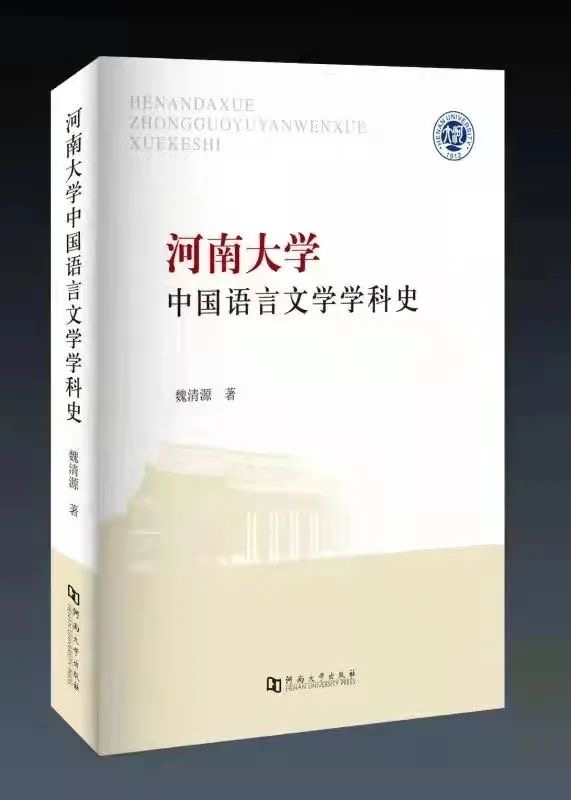
宏大叙事与精微考证:学科史书写的范式
《学科史》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其宏大的时间跨度和周密的结构安排。全书以编年为经,以专题为纬,清晰地勾勒出河大中文学科自1923年(中州大学时期)初创,历经省立中山大学时期、省立/国立河南大学时期(含抗战流亡)、院系调整后的师范学院时期(河南师范学院、开封师范学院),直至改革开放后复名河南大学并迈入新世纪,直至2022年的完整发展轨迹。这种宏阔的百年视野,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学科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发展脉络、制度变迁、人事更迭与学术风貌。
作者并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线性叙述,而是借鉴了成熟的机构史研究范式,在每个大的历史分期下,皆设有“学科沿革”、“教师队伍”、“教学科研”等核心板块。这一结构设计极具匠心。“学科沿革”部分侧重于制度层面的变迁,如系科设置、学制改革、课程演变、机构合并分立等,清晰地展现了学科组织形态的演化;“教师队伍”部分则聚焦于“人”这一学科发展的核心要素,不仅记录了各个时期执教于此的名师硕彦,更通过对师资结构、来源、流转的分析,揭示了人才汇聚与流散对学科兴衰的深刻影响;“教学科研”部分则关注学科的内在生命力,通过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科研成果、学术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描述,呈现了学科在不同阶段的学术追求与贡献。这种结构既保证了历史叙述的连贯性,又突出了学科史研究的关键要素,使得全书骨架清晰,血肉丰满。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学科史》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从目录中详尽的章节设置,以及附录部分包含的“毕业生名单”、“历任党政领导名录”、“文学院沿革图”等内容,可以窥见作者“爬梳众多资料,历经千辛万苦”的严谨治学态度。可以想见,书中必然大量征引了校史档案、系科文件、教师著述、学生回忆、报刊资料等第一手文献。这种对史料的精细考证和审慎运用,使得本书不仅是一部叙事史,更是一部具有高度文献价值和档案意义的参考工具书,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不仅仅是“述”,更包含了大量的“考”,体现了史学研究求真求实的精神。
学运与国运:百年学科的命运交响
关爱和教授在序言中提出的“学运关乎国运”之论断,可谓点睛之笔,也构成了理解《学科史》的一条重要线索。魏清源教授的叙述,并非将河大中文学科置于真空之中,而是始终将其嵌入到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中加以考察。学科的创立,正值“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旧交替之际;其成长,则伴随着北伐战争、抗日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其转型,则深受建国初期院系调整、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其复兴与壮大,则与改革开放、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息息相关。
书中对几个关键历史节点的处理,深刻地揭示了学科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同频共振。例如,抗战时期(1937-1945)“烽火办学”一章,必然细致描绘了学科随学校辗转流亡于鸡公山、镇平、嵩县潭头的艰苦卓绝。在“国家多难,文化薪传不绝”的背景下,弦歌不辍,坚持教学科研,并最终在流亡途中获得“国立”称号,这本身就是一曲知识分子坚守精神家园、维系文脉于不坠的悲壮赞歌。《学科史》对此段历程的记述,不仅是对河大中文学科韧性的展现,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颂扬。
同样,书中对1949年后,特别是1952年、1956年两次院系调整对学科造成的巨大冲击,也必然有所着墨。关序中以“折枝成林”形容这一时期,虽带有些许无奈,却也点明了历史的复杂性——河南大学主体虽遭削弱,但其分出的力量却滋养了中南乃至全国的多所高校。学科从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转变为师范院校的中文系(先是河南师范学院,后是开封师范学院),其学科定位、培养目标、师资结构、研究重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学科史》对此段历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宏观背景及其对单一学科发展轨迹的具体影响,也更能体会到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以及新世纪以来重返国家队行列(省部共建、“双一流”)的非凡意义与历史必然性。
学人与学术:名师荟萃与薪火相传
“学术系于学人”,学科史的核心终究是人的历史。《学科史》的另一大亮点,便是对“教师队伍”的浓墨重彩。从目录和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星光熠熠的名师谱系。
学科初创时期,冯友兰这位哲学巨擘亲自擘画,奠定了学科的初步格局。其后,郭绍虞、董作宾、嵇文甫、段凌辰等第一代学者筚路蓝缕,开创基业。冯友兰提出的“输入新学术、整理旧学问”以及培养“像样大学的教员”的理念,在书中有详细阐述,这无疑为河大中文学科奠定了注重学术研究、强调学者主体性的优良传统。
三十年代,随着学校升格为省立河南大学,学科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刘节、姜亮夫、高亨、朱芳圃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高材生,以及缪钺、卢前(冀野)、邵瑞彭(次公)、罗根泽、江绍原等名家纷至沓来,一时“名师云集,群星璀璨”。书中对这些学者的学术活动、治学路径(如国故整理、诗词曲赋研究、甲骨学研究等)、师生互动(如邵瑞彭对学生于安澜的提点)的记述,生动再现了民国时期大学相对自由开放的学术生态。
抗战及以后,尽管条件艰苦,但于赓虞、张长弓、任访秋、李嘉言等学者,以及稍后的高文、李白凤、万曼、于安澜、华锺彦、刘纪泽、钱天起等中坚力量,赓续学脉,各有建树。《学科史》对这些学者的坚守与贡献的记录,尤其是在逆境中取得的学术成就(如李嘉言、高文等主持的《全唐诗》整理与索引工作),感人至深。
书中对“名师”的关注,并非仅仅罗列名单,而是力图通过展现他们的学术旨趣、治学方法、教学风格乃至人生遭际,勾勒出学科精神的传承与演变。从冯友兰的哲学思辨,到郭绍虞、罗根泽的文学批评史,董作宾、朱芳圃的甲骨学与古文字学,再到李嘉言、高文的文献整理,任访秋打通古今的文学史研究,以及华锺彦、于安澜的诗词吟咏与书画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河大中文学科深厚的文史哲底蕴和多元并包的学术气象。
传承与特色:百年学科的成就与展望
历经百年风雨,河大中文学科不仅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更在诸多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关爱和教授在序言中点出的唐诗整理与研究、《文选》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明清文学研究、语言文字学研究等,在《学科史》中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唐诗整理与研究,自李嘉言先生发轫,高文、佟培基等几代学人持续耕耘,《全唐诗》各种索引的编纂,为全国唐诗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奠定了河大在此领域的重镇地位。书中对此项持续数十年的学术工程的记述,本身就是一部学科建设与团队协作的生动案例。
《文选》研究,从早年的段凌辰,到当代的王立群等,薪火相传,成果斐然。尤其是王立群教授领衔的“《文选》汇校汇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必将成为新世纪《文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则呈现出与古典文学不同的发展路径。任访秋先生打通古今,开近代文学研究之先河;刘增杰、刘思谦等学者则在解放区文学、当代小说、女性文学等领域深耕细作,影响广泛。《学科史》在梳理这些优势方向的形成过程时,也揭示了学科内部不同研究范式、研究路径的互动与发展。
此外,甲骨学、音韵学、训诂学、民俗学、文艺理论、比较文学等方向,也都曾有过名家执教,或形成了特色研究。《学科史》的全面梳理,有助于我们完整地认识河大中文学科的学术版图及其深厚积淀。
结语与思考:百年坚守,百年辉煌
总而言之,魏清源教授的《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史》是一部规模宏大、史料翔实、结构严谨、视野开阔的优秀学科史著作。它不仅是为河大中文学科百年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特别是地方院校学科发展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贡献。它为我们理解一个学科如何在时代洪流中生存、发展、转型、复兴,如何在一代代学人的坚守与开拓中形成自己的传统与特色,提供了宝贵的范例和丰富的史实。
掩卷之余,亦有几点思考。首先,学科史的书写,如何在肯定成就、颂扬传统的同时,保持必要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特别是对于历史上某些特殊时期(如反右、文革)对学科和学人造成的创伤,《学科史》是否给予了足够坦诚和深入的剖析?其次,在“教师队伍”之外,“学生”作为学科历史的亲历者和未来学科的承继者,他们的学习生活、思想变迁、社团活动等,是否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再者,除了纵向的历史梳理,学科史研究是否可以引入更多横向比较的视野?将河大中文学科置于全国同类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下,其特色与不足或许能得到更清晰的映照。
当然,这些思考并非苛求,一部皇皇巨著已然展现了作者巨大的付出和卓越的识见。这部《学科史》,对于河南大学的师生校友而言,是一部寻根溯源、凝聚认同的精神家谱;对于高等教育史和文学史的研究者而言,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对于所有关心中国教育与文化命运的人而言,它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样本,印证着“百年坚守,百年辉煌”的真谛。我们有理由相信,承载着百年厚重历史的河大中文学科,必将在新的时代,续写更加华彩的篇章。
相关链接:
关爱和序《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史》:百年坚守 百年辉煌
魏清源著《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史》:名师荟萃,群星璀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