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学衡派”编年文事》之后,想对民国(特指1912—1949年这一时段)学术的几个兴奋点进行重新阅读、叙事。于是就选择相对熟悉的大学文脉、首届院士、教授荣誉进行档案查阅,并试图进入民国学术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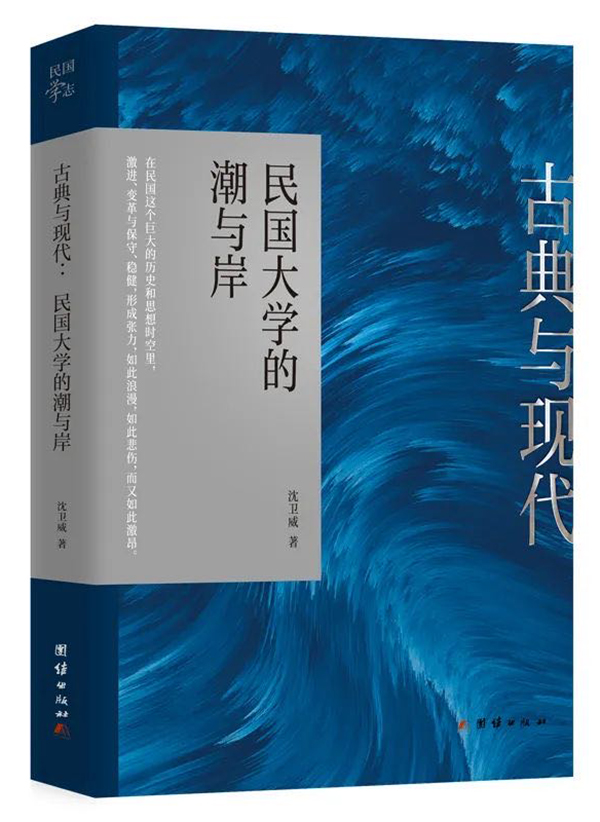
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我只是在民国大学之中,特别是南北两所代表性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差异性上,由文入史,关联人事,进行解读、讲述。我不求全面,有意设置话题,突出差异,然后在情景叙事中解答。
有意设置一组对立或差异性关键词:异口同声、顺势逆反、旧学新知、雅言俗语、学分南北、积极消极、古典现代、激进保守等,在南北两所大学,寻求史实,并关联相近大学的人事,展示文学与学术演进脉络。最后利用档案,讲述危急时刻大学的南渡西迁。
大学内部,校长、教师、学生,乃至工友,本是丰富多彩的互动场所,也是有风雅故事的地方,文学呈现,有诗歌、小说、散文或戏剧形式。当往日的大学成为历史,驳杂繁复的史料,乃至各类逸闻趣事,笑话八卦,这些虽说是回不去的从前,却都是我关注的东西。这本谈论民国大学文脉与随后谈论院士、教授的《教授与院士:民国教育的文与质》,我都在呈现史实的同时,有意将人性、人情与趣味一并加进,自将磨洗,行文策略为情景叙事,而非分析推理。这也是我多年来见人见物,质立文随,求行之远,更求好读的行文追求。江清月近人,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更容易与读者接近。
本书写作时间较长,尚未完成时,便于2014年,将一半内容,先行以《民国大学的文脉》为题,作为一册小书,在大陆、台湾同时刊印。这里将新写出的五章并入,并对原来的文字进行较大删改,成一本完整的《古典与现代:民国大学的潮与岸》。
“民国文脉”这一融合学术史与文学史的研究路向,是我长时段的一个学术关注点。我试图重返民国历史现场,通过重新叙事,梳理大学文脉,把握人文理路,明晰民国学统。
在民国这个巨大的知识和思想的时空里,首先是外敌入侵、残酷的党争、内战以及自然灾害笼罩,谁也摆脱不开。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首先是驱除外敌,结束内战,进而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重建。旧有的道统、学统和家法,新学的科学、民主、自由理念,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需要被一个整体包容的氛围,有条件地吸收、整合。延续晚清一些学理之辩,如华夷、汉宋、古今、中西、新旧、有用无用,已经被一些新的政治观念和国家话语如主义、政党、革命、反革命、战争、和平、解放所取代,或被王国维这样的学者主动放弃。在这个学术与政治纠缠,公德与私情纠结,个体与社会、家国难分的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的个人担当和国家、民族对个体的责任,都无法说得清楚,甚至谁都不能完全兑现各自的承诺。因此才会有种种矛盾、对立和不公平。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都是后来探究者所必须正视的。了解的同情固然是一个好的托辞,同时也要提醒自己,事实本身不容以任何理由人为地遮蔽,特别是国共两党之争和日军侵华这两个无法绕过的历史事实。我以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主要考察对象,还原历史语境,本着为见树木,必入森林的原则,力求通过多个关键词和兴奋点,揭示民国大学文脉与学统间复杂的内在关联和理路,并感受细节的力量。当然,民国大学的丛林很多,我关注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进入民国大学丛林的路径很多,我走的只是属于自己的这一条。
晚清以向西方学习为基本路径的维新变法,对文化教育最为直接的冲击就是1905年9月2日科举废,学堂兴。这是汤因比文明论“冲击—回应”模式中所谓“主动建设性的大策略”,是国家政治行为中重大的文化教育变革,完全有别于之前民间被动性接受传教士的传教办学模式。教育模式发生如此重大变革,直接改变了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晋身方式,也为与世界交往开辟了新路。私塾、书院、科举废除,特别是国外现代大学办学模式和教育理念的移植,给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教育体制变革是显性的,而传统士大夫内心撕裂却是隐性的。通常认为传统士大夫,或遗老遗少隐隐作痛的发声是旧文学,留学生和新青年欢呼雀跃的呐喊是新文学。所不同的是语言表现形式:文言与白话,或雅言与俗语。两种不同的路向,在抗战的特殊年代,又因民族危机,而呈现相互包容共生,求同存异的事态。
从京师大学堂时取法日本,到蔡元培取法德国,再到郭秉文、蒋梦麟、胡适等取法美国,李石曾取法法国,教育家在逐步探索中,为中国高等教育开启多元共生的新局面。因此,我以为中国大学兴盛的头功应记在归国留学生名下。其中作为交流的语言工具,因“有科举的维持,故能保存二千年的权威”的古文也逐步转变为白话。教育是兴国立人最为基础性方式,它不仅使人摆脱蒙昧,而且逐步改变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如果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改变,一人一家皇权统治瓦解也就为时不远了。自1905年9月2日科举废除始,6年过去,276年的王朝就分崩离析。随着民国新建,大学体制形成和初具规模,中国社会从几千年“官学”与“私学”并存的教育形态,向国民“公学”的公民社会转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国民教育公共空间的变化,是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建设基础。小学与中学建制,这里不讲。本书会先讨论进入民国大学的路径,然后,再选择性地就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一些有趣的话题展开。
“大学”这一外来文化教育模式,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需要时间,需要有人来培育。因此,除政府财政扶植和民间资本(私人财团和教会)资助外,蒋梦麟所说的大学内部校长、教授和学生三种力量,通常也会形成一种互相促进和互相牵制的合力,成为大学的自身力量。
(本文是沈卫威新著《古典与现代:民国大学的潮与岸》自序与绪论合编。该书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沈卫威,1962年2月生,河南省内乡县人,文学博士,1991-2001年执教于河南大学,2002年始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无地自由——胡适传》《望南看北斗——高行健》《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大学之大》《民国大学的文脉》等。《学衡派年谱⻓编》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