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把全人类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并且为此日夜不安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济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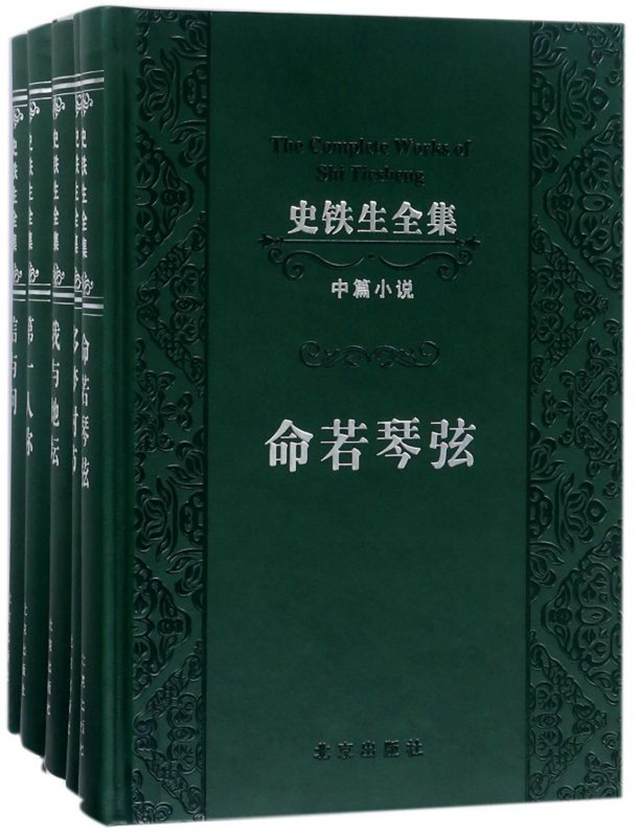
他不会走远
今天,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家与哲人史铁生71岁。他已经离开我们11年又四天了。
上周末,身边的一位朋友说:如果必须精选,他会用三篇文字讲解生命哲学与生命教育: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笔者当时就想,是否可以开一门通识课:当代文学经典与生命意识——就从史铁生切入。
可惜,这位用苦难洗净世界,用文字守护灵魂的作家活着的时候,我没有见过他,2000年3月,为写河南艾滋病的深度报道,我去过北京地坛医院的艾滋病房采访。知道不远处就是他的住处,很想去找他,但时间太紧,又过于唐突,没有去。
然而,他却是与我很近的人。我读完了他所有的文字,收藏了他的各种版本的著述。我的书房、卧室、办公室里都有他的影子。从1983年年初,他带着他的遥远的清平湾走进我的生活、我的生命,从来没有离开也不会再离开我。
那一年,读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篇末——“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20多岁的我流泪了。白老汉不知道陕西粮票在北京不能用,他卖了十斤好小米,换了那粮票,为了“我”治病时会用得上。我觉得那不是小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细节的真实性。
再后来,读到《命若琴弦》,我震撼了。连续读了一个星期,书页上密密麻麻批满了小字,后来评上教授,用的就是写这部小说的文字。记得彼时南京师大推荐给学生的“史铁生研究”参考论文里还有那篇。
多次出差,我带着他的书,使得漫长的旅途变得温馨、充实。是他叫我明白了如何做镀亮灵魂的朝圣者、丰腴灵魂的布道者、滋润灵魂的沐浴者——如何让平凡甚至贫瘠的生活距离上帝更近。
所以,他是我的亲人,我的兄长,我的心理医生。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他悄悄地走了,他的背影让新年的阳光更加温馨。
今年元旦的凌晨四点,我已经起身,开窗温馨的看看夜色,想起陈村曾经的提议:请中国作协负担史铁生的医疗费用。
呜呼!有多少假作家、伪作家、拿纳税人的钱买回的作家踵事增华,而史铁生走了。
我只有用阅读与心得纪念他,祈祷天国里没有“透析”二字。
借纸笔悟死生
与西哲们以小说戏剧挥洒其哲学观念相反,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默默耕耘的中国小说家,试图告别一般意义上的故事和抒情而悄悄跨入哲学的门槛,甚至企图回答“此行何去”等元问题,欲在更高而更深的意义上深入人心,切入历史。
陈西滢陈教授指责鲁迅“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相仿,史铁生序洪峰的《瀚海》,或许可以理解成为自己抒情:“我看洪峰这个人主要不是想写小说,主要是借纸笔以悟死生,以看清楚人的处境,以不断追问那个俗而又俗却万古难灭的问题——生之意义。文学的起点不应该是诺贝尔文学奖。假设人类穷尽了“生之意义”这个命题,文学肯定会以二分钱以下的价格被拍卖。”
以自己的生命参悟世界,探究别人和自己的存在,在这里,写作已是一种生存方式,其背后是一连串沉重又又沉重的思索。因此,讲完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山顶上的传说》之后,史铁生从自叙传的黄土高原上走了出来,深情地虚构了莽莽群山中两个瞎子的故事:“莽莽苍苍的群山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攒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也无所谓到哪儿去,每人带一把三弦琴,说书为生。”
“○者,无极而太极也。”或许正因为宇宙运行的轨迹是起点与终点相连接的圆,小说的结尾完全又回到了开头,且将末句改为: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
“篇终接混茫”,这种隐现于写实与荒诞、聊天与悟道之间的文字,一下子把我们拖进了渺无人迹的莽莽群山,让我们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中深深体味“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到哪里去?”的欲解脱而不得、情深思苦的宗教境界。当我们蓦然回首,或许会吃惊地发现: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自己莫非也是一个匆匆忙忙的瞎子?
象征主义
三十年前,评论家把《命若琴弦》编入《象征主义小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提示。的确,“群山”、“走路”、“琴弦”、“瞎子”、“药方”,无不包含着太多太多的难以言传的丰富情景和象征意味。然而,谁又能否认这是作者以“真人真事”的姿态与我们倾心交谈?谁能说老少瞎子仅是“象征”而不是生命欲四溢的活人呢?用传统的文论概括,《命若琴弦》的“基调”又实在是“立足现实”的,大可以归入“民族文化派”。同时,如果说中国的“结构主义”小说侧重“形而上”的生命本体意义的追寻,则《命若琴弦》又恰恰表现了极浓烈的生命感觉,极丰富的内心体验,极严肃的关于本体存在价值的“形而上”思考。因此又不难跻身于“结构主义小说”之列。然而,从阐释和体验的角度上说来,《命若琴弦》作为象征小说,正好为阅读者留下了神游乎六合的广阔天地。文字背后的含义为联想所填补,为遐思所演绎,使读者于“解构”的同时也拨响了自己的生命之弦、审美之弦。
伽达默尔说:“由此,艺术作品就被理解为生命之完美的象征性再现,每一种体验似乎正走向这种再现,因此,艺术作品本身就表明为审美经历的对象,这便得出一个美学结论:所谓的体验艺术则是真正的艺术。”
其实,见仁见智,连“象征”二字也是因读者而异的。对于这一部分感觉着“微雨夜来过”却依然“不知春草生”的读者,弹琴与生存、琴弦与命运、赶路与追寻过程并未构成对应关系,无非是老瞎子上了师父的当,辛辛苦苦奔波了半个世纪,终于发现可以让自己重见天日的药方只是一方白纸,而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欺骗了自己的徒弟小瞎子而已。可是对于“前不见岸,后也远离了岸”,而且“一停下来就会变成石头”的远足者,小说中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都会拨响他们记忆中的交响曲。对于那些“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先天和后天、眼睛和心灵的失明者们,“走”和“弹琴”三个字下面,该有多少美丽而凄凉的故事!
生命=行走之和
“莽莽苍苍的群山中走着两个瞎子。”小说的第一句,已经定下了悲剧的基调,这是一个孤独地跋涉于莽莽群山丛中的探寻者的悲剧,是一对盲人“敢问路在何方”的悲剧。这第一句的重要性颇类似于《百年孤独》中的第一句:“许多年之后,面对刑警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评论家说此句用“过去将来完成进行时”纵横古今,唯有大手笔可以写出。
史铁生是凡人,只能用“过去进行时”,可这第一句已足以让我们记起“我只要我的现在”的鲁迅先生。
“请不要将我们打扰。时间正飞驰而去,而转瞬之间我们的双唇就会永闭无声。”正因为意识到了生命的紧迫感,鲁迅笔下的那位“过客”才无数次地重复着“我只得走”、“我不回转去”、“还是走好”的语句。虽然饱经风霜的老翁明明白白地告诉这位过客前面只是坟,是无一人可以例外的“死亡”,但过客终于脚步踉跄地走了下去。那“过客”正是鲁迅本人。作为“历史的中间物”,他在明与暗、生与死、爱者与不爱者之间背负起因袭的重担,孤独而顽强地跋涉在清末民初那“莽莽苍苍的群山中”。于是他说只有黑暗与虚无才是实有,他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向那“无物之阵”举起了投枪,进行着自己“绝望的抗战”。
至此,“走着无尽无休的无聊的路”的老少瞎子,“以现在治现在”的鲁迅师徒,与高扬“行动哲学”的萨特殊途同归了。萨特说:“社会理想,究竟会不会实现,对于这一点我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只是我尽力使之实现,过此则不能计及”。走下去,然后再说意义,“存在先于本质”,意义恰在于行走之中。
的确,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乌托邦式的空想和奥波罗摩夫式的懈怠已经给予人类太多太多的教训。不浸身于真实的跋涉的苦难,不踩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节奏“走”下去,便只有阮籍似的恸哭而返,只有世故老翁似的“回转去” ——再一次落入那嬉笑着的名目、驱逐、眼泪和牢笼的漩涡。
当然,还是史铁生本人的解释更为明晰:“无限的坦途与无限的绝路都只说明人要至死方休地行走,所有的行走加在一起便是生命之途,于是他无惧无悔不迷不怨认真于脚下,走得镇定流畅,心中倒没了绝路。这便是悟者的抉择,是在智性的尽头所必要的悟性补充。”
而且,史铁生发现,这种“走下去”的“宗教精神”并不敌视智性、科学和哲学,“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际,代之以前行”。“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北岛) ——探寻者的足迹永远是绯红色的,无论有没有尽头,只要有人坚定地走下去,那生命之旅途上便会“飘满红罂粟”。
无中生有
鲁迅笔下那位“过客”的希望,虽则扑朔迷离,却是神力无穷:“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那“声音”正象征着希望和诱惑。相比之下,老少瞎子的希望似乎真实得多:“能看一回,好好看一回,怎么都是值得的。”殊不知过客的“听”和瞎子的“看”终不过同是虚无飘渺,是自己善良的愿望所铸成的幻影。再扩而大之,不跛不瞎而不可一世,甚至似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鲜花著锦”而“烈火烹油”又能如何呢?结果不依旧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吗?
活着或者不跛不瞎地活着并不意味着一切。倘若没有一种“走下去”的精神力量去抵御命运的定罚,无论何人都不会比老少瞎子们更其幸运。倒是老庄略胜一筹,道破了天下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四壁中空,方有房屋,器皿中空,方可实用。“可见谓之有,不可见遂谓之无,其实动静有时而阴阳常在,有无无异也”。
“我想睁开眼看看,师父,我想睁开眼看看!哪怕就一回。” “你真那么想吗?” “真想,真想——” “那就弹你的琴弦,”老瞎子说:“一根一根尽力地弹吧。记住,得弹断一千二百根。”
于是,老瞎子生命的“熄灭”、希望的“无”,变成了小瞎子绷紧的琴弦,变成了“复明有望”的“有”。无论是师傅还是徒弟,“有”的破灭和它的实现在相同的时间空间,以相同的形式完成了,这无疑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悖论。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如果说小说开始时是一种神秘而平淡的介绍语气,那么类乎开头的结束便是走入虚无且是走出虚无的悲壮,这里的超越时间与空间、起点与归宿甚至“无所谓谁是谁”的“走”,是临刑,也是将婚;是行刺,也是朝圣;是赴约,也是失恋;是踌躇满志,也是万念俱灰。其激动人心完全不下于那首奥运会的主题歌:“每当我们出征,熊熊的火焰燃烧在我们胸膛。”
顿悟于极限
20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德日进说:“我知道只有当我达到努力的极限时,神才会向我显示他自己。只有当我像雅各那样被神打败的时候,我才会真正接触到神的实在。”——老瞎子也正是这样,当他一下子明白了自己为之奔波了半个世纪的复明之药方乃是一方白纸的时候,当“吸引他活下去、唱下去、走下去的东西骤然间消失干净”时,他达到了自己全部能力的极限,败倒在命运老人脚下。他的心死了:“面容也憔悴,呼吸也孱弱,嗓音也沙哑了,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感觉到自己在一节节地熄灭,因此他“骨头一样的眼珠在询问苍天,脸色也变成骨头一样的苍白”。——像绝望的屈原夫子、刑余的太史公、写作《野草》之际的鲁迅,老瞎子虽然还“活着”,但其精神或曰灵魂却已经真真切切地“死”过了一回。他必须绝望,他必然绝望,他没法不绝望。
然而,恰在绝望之际,他“顿悟”了,他一下子明白了以往那些奔奔忙忙,那些兴致勃勃地翻山、赶路、弹琴、乃至心焦、忧虑,都是那么快乐!那时有个东西把“弦”扯紧,虽然那东西是虚设。老瞎子想起他师父临终时的情景。他的师父把那张自己没用上的药方封进他的琴槽:“你别死,再活几年,你就能睁眼看一回了。”说这话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师父久久不言语,最后说:“记住,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不错,那意思就是说:目的本来没有。重要的是从那绷紧的过程中得到欢乐。
至此,可以说老瞎子那五十年的生命之弦没有白弹,五十年的汗水和琴声不是白纸,不是虚无。尽管他永远睁不开那骨头一般的眼,可他一定听到那个浑厚的声音:“你走上了达到你的伟大的路!自来你的最危险的、现在成为你的最后的庇护所!你走上了达到你的伟大的路,现在临于绝地便是你的最高勇敢!”(尼采)
其实,“哲学最崇高的努力,至多不过是隐隐约约地指出欲望、希望,或者顶多也仅仅揭示一种未来状态的可能性”(吉本)。为了那“只须一伸手,金苹果就会落下”的美丽的希望努力过,挣扎过,死过和活过,这也就够了。写出《命若琴弦》六年之后,史铁生在其一篇重要散文《好运设计》中再明白不过地解释了“顿悟于极限”的内涵:“……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你依然没有玩够,但你却不惊慌,你知道过程怎么能有个完呢?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巧妙的设计。”
这正是“西绪弗斯神话”的活写真,既然“每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那他的苦难又将在哪里?”加缪说:“我让西绪弗斯留在山下!人们总是看得见他的重负。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弗斯是幸福的。”因此,顿悟于极限所在地的老瞎子也是幸福的,于不知不觉中直奔极限的小瞎子更是幸福的。
满足与超越
读完老少瞎子“边走边唱”(陈凯歌以这四个字为名将《命若琴弦》改成电影,可惜至今笔者没有看到)的故事,有心的读者不难联想起海因里希·伯尔精彩的小小说《优哉游哉》:欧洲西海岸某码头上,一个衣衫褴褛的渔夫在破船中闭目养神,一位时髦的游客搅醒了他并劝告他说:如果每逢好天你都多出几次海,过一年你就可以再买一台发动机,两年就可以添条船,将来可以建起自己的冷藏库,熏鱼厂,以至于用直升飞机寻找鱼群,用无线电指挥机动船——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渔夫问成了百万富翁之后怎么样,游客描述曰:“然后,你就可以优哉游哉地坐在码头上,在阳光下闭目养神”。渔夫的回答是:“现在我已经这样做了。”——如果不是你搅醒了我,我大概还在继续优哉游哉地闭目养神!
的确,转了整整一圈儿,终不过“优哉游哉”而已,因此老少瞎子翻山越岭艰苦跋涉,去苦苦追寻那本不存在的希望,实在是多此一举。
然而,人的崇高之处或曰那种宗教精神的魔力恰恰在于对于人自身有限性的超越——既包括对于死亡、绝望、虚无、谬误的超越,也包括对于惰性、贪欲、“优哉游哉”的超越。不愿意起身“走动”一下的渔夫,是永远想不到超越也超越不了他自己的,因为他将终生不知道何谓绝境和极限。与其相反,老瞎子却于日暮途穷之际把一轮希望之火传给了徒弟。他赶路弹琴的过程正是“诗化”而“灵化”自己的过程,尽管他依旧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把你的琴给我,我把药方给你封在琴槽里” ——此际,我想到的是:“人,诗意地栖居”。老瞎子的存在无疑是一首苍凉悲壮的诗。绝望的老瞎子恰恰诗意地存活于为徒弟提供意义的意义之中。“传薪”的同时,也为人间提供了一种悲壮的死法或者活法,并因此使我们生存的这个充满情感却缺乏真情的世界多了一丝温暖的诗意。
当然,对于公正得近乎冷酷的时间老人说来,老瞎子的今天便是小瞎子的明天,“超越”与否也只近于理念世界的空想。可是从“说书人”到“诗人”的过渡中,老瞎子存活的质量却陡然增加了——这又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正是从这个“为世界增添意义”的意义上考察,唯有渔夫一样的满足没有“药方”可救,他将永远优哉游哉,永远不会有失望的苦楚和极限的恐惧,可这种满足的代价是不知道阳光下还有“撄人心”的、叫人感受到生命活力的追求过程的满足。
面对情感世界
“情之一字,所以维系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
从小说的描写看,作为艺人和“诗人”的老瞎子无疑体验过那个叫做“爱”的东西。他对暗暗想着兰秀儿姑娘的徒弟说:“听我一句话,保准对你没坏处。以后离那妮子远点。”“早年你师爷这么跟我说,我也不信” ——并非因为女人是“祸水”、“尤物”而近不得,倒是正因为不是祸水、不是尤物所以尤其迷得住凡人好人与“粉饰乾坤”的艺人。
恰恰就在老瞎子以亲身经历的痛苦体验劝说徒弟的当晚,他自己也心猿意马,浮想联翩,差点儿走火人魔,以至于琴声乱得一塌糊涂。他敏锐地感到将要“犯病” ——半个世纪积淀的心病。于是,为抵御情感世界的波涛,他只有把最后也是最厚的一块盾牌拖了出来:“他只好再全力去想那张药方和琴弦:还剩下几根,还剩下最后几根了。那时就可以去抓药了,然后就能看见这个世界——他无数次爬过的山,无数次走过的路,无数次感到过她的温暖和炽热的太阳,无数次,梦想着的蓝天和星星……”
似乎这一切足以让他“移情”,使他从“病魔”的纠缠中脱身。
可他即刻又感觉到盾牌的不够坚厚:“还有呢?”突然心里一阵空,空得沉重。只就为了这些?还有什么?他朦胧中所盼望的东西似乎比这要多得多。
到这里,悖论再度出现了。“在那些爱思索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喜剧,在那些重感情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悲剧。”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智者,老瞎子是睿智的思想家,他深知自己在情感世界中的无力,深知一生仅有赶路和弹琴的过程,此外不二法门。可偏偏他的信仰又无法彻底——一旦涉足情感世界,他的几十年铸就的经验和世故便糖塔般地迅速瓦解了。他明确地意识到:失去的已永远失去了,再也不能回到身边。在坦然步入虚无又超越虚无的悲壮历程中他得到了多少,则在得不到所爱又无法忘却所爱的情感世界中失去了多少,他可以瞒过徒弟,但他瞒不过自己和自己手里的三弦子。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确实,70岁了再疯实在没有意思。即便双目如炬,又到哪里去搜寻当年的兰秀儿呢?又如何去重新体验那让人骤然生动的一切呢?过程就是一切的反命题恰是过程中流逝了一切,毕竟还有睁大双眼也无法找回的日子——那让人铭心刻骨、融入血液的日子啊!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且,恰恰是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人们才能驰骋诗意的幻想。因此,面对情感世界,我们对于浩叹齐天的老瞎子和为兰秀儿唯求速死的小瞎子当然不敢轻薄半句,那位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名言或许是老瞎子师徒“行状”最好的注脚:“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才能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为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广义残疾
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所需。
小瞎子之所以那么顽强地期待着“看一眼”,与他心头那抹不掉的兰秀儿的身影有直接关系。吴俊先生在透视史铁生创作心理时发现了史铁生小说的“残疾主题”。
其实,从十年前史铁生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对牛的描写中,我们已经感到了那种“被同类遗弃”的沉重:那匹老黑牛有过可歌可泣以至于“三宫六院”的过去,但它后来默默地被挤出了圈儿外,作者几乎是含着泪为它送葬的。而与残疾主题如影相随的便是性自卑,“性爱主题是一种使史铁生的灵魂不得不受到拷问和折磨的小说主题”(吴俊),他一边同样对于性爱和爱情充满了渴念,同时又基于残疾人的体验和感受,对性爱及其描写表现出敏感的悲观和恐惧。而且,他没有“移情”于作品中美丽的女性,而是“把正常的性欲望压抑到潜意识中,或以一种对性爱的排斥甚至否定形式表现出来”,作为心理的补偿和焦虑的缓解。
重要的是,道出了残疾人处境和心境的史铁生并没有一味地呼唤:人啊,理解我们吧!从而换取一掬同情的泪水。鲁迅的《铸剑》中,复仇主人公黑衣人严冷地对眉间尺说:“孩子,你不要再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史铁生正是如此,不吃嗟来之食,不要布施的同情,他只求人格上的独立和完整,以一个自由人的形象与同类比肩而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他的侃侃而谈的小说中,总是能觉察到一股坚韧前进的阳刚之气。
非但如此,经历了伤残以至于自杀的炼狱的熬煎,史铁生再生了。他在写给《文学评论》编辑部的信中指出:“‘残疾’问题若能再深且广泛研究一下,还可以有更深且广的意蕴,那就是人的广义残疾,即人的命运的局限。”
在此,他以心灵的完整和充实提醒了所有心理上的残疾者,他密切关注的是幅员更廓大的伤痛。因为“命运”作为深不可测的必然正是人们“赶路”“弹琴”过程中无数个偶然的总和。在我们的四周,奴性、媚态、阴谋、专制、拜金、自私、妒嫉、阿Q无不证实着“广义残疾”的存在,无不造就着一些心理世界中的老瞎子和小瞎子,即精神盲人。
的确,“能看见正在眼前的东西是多么困难啊”。
严格地说,“广义残疾”或曰“心理残疾”并不是信仰即“宗教精神”的彻底失落。例如跪倒在权势和金钱脚下同样显示了饥渴而虔诚的“宗教精神”,但这些人崇奉的恰恰是一种坏迷信或曰“邪恶的宗教”。这种崇奉强化着、蔓延着、滋生着广义的残疾,而“广义残疾”同时又发展着、加高而且加厚着那邪恶的崇奉。
史铁生从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出发,通过发人深思的警醒,带着我们回到鲁迅先生为之奋斗终生的题目之上——改造国民性。我想,提出“广义残疾”的意图正在这里。
当然,史铁生洞若观火:借助他写小说的笔并不能彻底救治四周的“广义残疾”。可他明白他需靠那支笔生存下去,他力图用那支笔把人类的三种困境——孤独、痛苦和恐惧——变成“既是三种困境又是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他于是继续着自己的“边走边唱”,我们于是也回到本文“借纸笔悟死生”的开头。
谎言与勇气
好诗无不勾引起重读的渴望。
《命若琴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一直受到人文学者们来自不同角度的关注和阐释。墨哲兰先生1995年底又一次提及《命若琴弦》,但立足点却是“自我完善”的虚幻:“一代人落空了,知道了师道的虚假,同时也领悟到师教的良苦用心:为了使下一代瞎子在光明的追求中自我完善,不得不把揭穿了的虚假继续当作真实传承下去。”“难道人类除了骄傲得目空一切,又如此软弱得愚昧可欺,需要把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建立在一个谎言上?即便这谎言是善良的、真诚的、美丽的。”
的确,“真的猛士”完全有理由指责老瞎子自律的软弱、道德的虚假。然而,为什么退回内心的自我完善不能在精神界占有一席之地呢?老瞎子“美丽的谎言”难道不也是一种“神圣的缺席”吗?面对道德颓势那“莽莽苍苍的群山”,教化和自律即便是无力的甚至是虚假的,可对于老少瞎子不依然是一条生命的路吗?把这个“道德的形而上学”也抛却了,走与唱的瞎子们又凭借什么生存下去呢?
如前所述,走下去唱下去也是一种勇气,虚假的枝条上偏偏结成了真实之果。在历史和现实不容许“缺席”而必须直面的时刻,“自我完善”的确是无力的,信仰应该归结于行动。——出家二十多年而最有理由“缺席”的弘一大师面对日本人的屠刀转而不再“自我完善”,在圆寂的前一年,他居然写下:“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这种毫不踌躇毫不虚假的气节与当年遁迹空门的决绝同样令人肃然起敬。但是,在更多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的场景中,在那些教化和自律同样使人向善向好的时刻——如老瞎子之于徒弟,为什么就不能对“美丽的谎言”网开一面呢?
“人常想病时,则尘心渐减;人常想死时,则道念自生。”史铁生以其慈悲心肠,甚至不愿对笔下的人物加一个残酷的词语,其间的平静与智慧,与摧枯拉朽的“金刚触目”其实是异曲同工。
既然人的局限性成就了上帝,那么就让激励人们沿“过程”之旅走下去的谎言与勇气一同美丽吧。
2022年元月4日于广东文理职业学院紫荆楼
-----------------------------------------END-----------------------------------












|




